兰波(1854-1891),15岁就擅长写作拉丁文诗歌,掌握了法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格律。从16岁(1870)起,他常常外出流浪,和比他年长10岁的诗人魏尔兰关系亲密,但后来发生冲突,魏尔兰甚至开枪打伤了兰波。现存的兰波的诗有140首左右,主要在16至19岁期间所写。在兰波早期的诗中可以看出帕尔纳斯派的影响,后期诗作加强了象征主义色彩。主要诗集有《地狱的一季》、《灵光集》。
醉舟
当我顺着无情河水只有流淌,
我感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
吵吵嚷嚷的红种人把他们捉去,
剥光了当靶子,钉在五彩桩上。
所有这些水手的命运,我不管它,
我只装运佛兰芒小麦、英国棉花。
当纤夫们的哭叫和喧闹消散,
河水让我随意漂流,无牵无挂。
我跑了一冬,不理会潮水汹涌,
比玩的入迷的小孩还要耳聋。
只见半岛们纷纷挣脱了缆绳,
好像得意洋洋的一窝蜂。
风暴祝福我在大海上苏醒,
我舞蹈着,比瓶塞子还轻,
在海浪--死者永恒的摇床上
一连十夜,不留恋信号灯的傻眼睛。
绿水渗透了我的杉木船壳,--
清甜赛过孩子贪吃的酸苹果,
洗去了蓝的酒迹和呕吐的污迹,
冲掉了我的铁锚、我的舵。
从此,我就沉浸于大海的诗--
海呀,泡满了星星,犹如乳汁;
我饱餐青光翠色,其中有时漂过
一具惨白的、沉思而沉醉的浮尸。
这一片青蓝和荒诞、以及白日之火
辉映下的缓慢节奏,转眼被染了色--
橙红的爱的霉斑在发酵、在发苦,
比酒精更强烈,比竖琴更辽阔。
我熟悉在电光下开裂的天空,
狂浪、激流、龙卷风;我熟悉黄昏
和像一群白鸽般振奋的黎明,
我还见过人们只能幻想的奇景!
我见过夕阳,被神秘的恐怖染黑,
闪耀着长长的紫色的凝辉,
照着海浪向远方滚去的微颤,
像照着古代戏剧里的合唱队!
我梦见绿的夜,在眩目的白雪中
一个吻缓缓地涨上大海的眼睛,
闻所未闻的液汁的循环,
磷光歌唱家的黄与蓝的觉醒!
我曾一连几个月把长浪追赶,
它冲击礁石,恰像疯狂的牛圈,
怎能设想玛丽亚们光明的脚
能驯服这哮喘的海洋的嘴脸!
我撞上了不可思议的佛洛里达,
那儿豹长着人皮,豹眼混杂于奇花,
那儿虹霓绷得紧紧,像根根缰绳
套着海平面下海蓝色的群马!
我见过发酵的沼泽,那捕鱼篓--
芦苇丛中沉睡着腐烂的巨兽;
风平浪静中骤然大水倾泻,
一片远景像瀑布般注入涡流!
我见过冰川、银太阳、火炭的天色,
珍珠浪、棕色的海底的搁浅险恶莫测,
那儿扭曲的树皮发出黑色的香味,
从树上落下被臭虫啮咬的巨蛇!
我真想给孩子们看看碧浪中的剑鱼--
那些金灿灿的鱼,会唱歌的鱼;
花的泡沫祝福我无锚而漂流,
语言难以形容的清风为我添翼。
大海--环球各带的疲劳的受难者
常用它的呜咽温柔地摇我入梦,
它向我举起暗的花束,透着黄的孔,
我就像女性似的跪下,静止不动……
像一座浮岛满载金黄眼珠的鸟,
我摇晃这一船鸟粪、一船喧闹。
我航行,而从我水中的缆绳间,
浮尸们常倒退着漂进来小睡一觉!……
我是失踪的船,缠在大海的青丝里,
还是被风卷上飞鸟达不到的太虚?
不论铁甲舰或汉萨同盟的帆船,
休想把我海水灌醉的骨架钓起。
我只有荡漾,冒着烟,让紫雾导航,
我钻破淡红色的天墙,这墙上
长着太阳的苔藓、穹苍的涕泪,--
这对于真正的诗人是精美的果酱。
我奔驰,满身披着电光的月牙,
护送我这疯木板的是黑压压的海马;
当七月用棍棒把青天打垮,
一个个灼热的漏斗在空中挂!
我全身哆嗦,远隔百里就能听得
那发情的河马、咆哮的漩涡,
我永远纺织那静止的蔚蓝,
我怀念着欧罗巴古老的城垛!
我见过星星的群岛!在那里,
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
“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
啊,百万金鸟?啊,未来的活力?”
可是我不再哭了!晨光如此可哀,
整个太阳都苦,整个月亮都坏。
辛辣的爱使我充满醉的昏沉,
啊,愿我龙骨断裂!愿我葬身大海!
如果我想望欧洲的水,我只想望
马路上黑而冷的小水潭,到傍晚,
一个满心悲伤的小孩蹲在水边,
放一只脆弱得像蝴蝶般的小船。
波浪啊,我浸透了你的颓丧疲惫,
再不能把运棉轮船的航迹追随,
从此不在傲慢的彩色旗下穿行,
也不在趸船可怕的眼睛下划水!
(飞白译)
黄昏
夏日蓝色的黄昏里,我将走上幽径,
不顾麦茎刺肤,漫步地踏青;
感受那沁凉渗入脚心,我梦幻……
长风啊,轻拂我的头顶。
我将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动;
无边的爱却自灵魂深处泛滥。
好像波西米亚人,我将走向大自然,
欢愉啊,恰似跟女人同在一般。
(程抱一译)
元音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们,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
A,苍蝇身上的毛茸茸的黑背心,
围着恶臭嗡嗡旋转,阴暗的海湾;
E,雾气和帐幕的纯真,冰川的傲峰,
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
I,殷红的吐出的血,美丽的朱唇边
在怒火中或忏悔的醉态中的笑容;
U,碧海的周期和神秘的振幅,
布满牲畜的牧场的和平,那炼金术
刻在勤奋的额上皱纹中的和平;
O,至上的号角,充满奇异刺耳的音波,
天体和天使们穿越其间的静默:
噢,奥美加,她明亮的紫色的眼睛!
(飞白译)
奥菲利娅
1
在繁星沉睡的宁静而黝黑的的水面上
白色的奥菲利娅漂浮着像一朵大百合花,
躺在她修长的纱巾里极缓地漂游……
--远远林中传来猎人的号角。
已有一千多年了,忧郁的奥菲利娅
如白色幽灵淌过这黑色长河;
已有一千多年,她温柔的疯狂
在晚风中低吟她的情歌。
微风吻着她的乳房,把她的长纱巾
散成花冠,水波软软地把它晃动;
轻颤的柳条在她肩头垂泣,
芦苇倾泻在她梦幻般的宽阔天庭上。
折断的柳条围绕她长吁短叹;
她有惊醒昏睡的桤木上的鸟巢,
里面逸出一阵翅膀的轻颤:
--金子般的星辰落下一支神秘的歌。
2
苍白的奥菲利娅呵,雪一般美!
是啊,孩子,你葬身在卷动的河水中
--是因为从挪威高峰上降临的长风
曾对你低声说起严酷的自由;
是因为一阵风卷曲了你的长发,
给你梦幻的灵魂送来奇异的声音;
是因为在树的呻吟,夜的叹息中
你的心听见大自然在歌唱;
是因为疯狂的海滔声,像巨大的喘息,
撕碎了你过分缠绵温柔的孩儿般的心胸;
是因为一个四月的早晨,一个苍白的美骑士
一个可怜的疯子,默默坐在你的膝边!
天堂!爱情!自由!多美的梦,可怜的疯女郎!
你溶化于它,如同雪溶化于火,
你伟大的视觉哽住了你的话语,
可怕的无限惊呆了你的蓝色眼睛!
3
诗人说,在夜晚的星光中
你来寻找你摘下的花儿吧,
还说他看见白色的奥菲利娅
躺在她的长纱巾中漂浮,像一朵大百合花。
(飞白译)
牧神的头
在树丛这镀着金斑的绿色宝匣中,
在树丛这开着绚烂花朵的朦胧中,
睡着那甜蜜的吻,
突然那活泼打乱一片锦绣,
惊愕的牧神抬起眼睛,
皓齿间叼着红色的花卉,
他那陈年老酒般鲜亮的嘴唇,
在树枝间发出笑声。
他逃走了——就像一只松鼠——
他的笑还在每片树叶上颤动,
一只灰雀飞来惊扰了
树林中正在沉思的金色的吻。
(葛雷、梁栋译)
乌鸦
当寒冷笼罩草地,
沮丧的村落里
悠长的钟声静寂……
在萧索的自然界,
老天爷,您从长空降下
这翩翩可爱的乌鸦。
冷风像厉声呐喊的奇异军旅,
袭击你们的窝巢,
你们沿着黄流滚滚的江河,
在竖着十字架的大路上,
在沟壕和穴窟上,
散开吧,聚拢吧!
在躺着新战死者的
法兰西隆冬的原野,
你们成千上万地盘旋,
为着引起每个行人的思考!
来做这种使命的呐喊者吧,
啊,我们穿着丧服的黑乌!
然而,天空的圣者,
让五月的歌莺
在栎树高处
在那消失在茫茫暮色的桅杆上,
给那些人们做伴,
一败涂地的战争
将他们交付给了
树林深处的衰草。
(葛雷、梁栋译)
童年
Ⅰ
这个黄毛黑眼睛的宠儿,没有父母,没有家园,比
墨西哥与佛拉芒人的传说更高贵,他的领地是青青野草,
悠悠碧天,他在海滩上奔跑,无船的波浪曾以凶悍的希
腊人、斯拉夫人和克尔特人的名义为海滩命名。
来到森林边缘,——梦中的花朵“叮当”闪亮,——
橘色嘴唇的姑娘,跪在浸润牧场的洪水之中,彩虹,花
草和大海在她身上投下阴影,绐她赤裸的身体披上青衣。
女人们在海滩上闲逛,女孩们和身材高大的姑娘在
青灰的泡沫间黝黑放光,宝石散落在解冻的花园与丛林
的沃土之上,——年轻的母亲和大姐姐们眼含朝圣者的
目光,苏丹王后和雍荣华贵的公主们步履翩跹,还有外
国小姑娘和含着淡淡哀愁的女人。
多烦愁,满眼尽是“亲近的身体”和“亲切的心”!
Ⅱ
是她,玫瑰丛中死去的女孩。——已故的年轻妈妈
走下台阶。——表弟的四轮马车在沙地里吱吱作响。——
小弟弟——(他在印度!)在那里,面对夕阳,站在开
满石竹花的牧场上。——而老人们,已埋在紫罗兰盛开
的城墙下。
蜂群般的落叶围绕着将军的故居。他们正在南方。
——沿着红色的道路,人们来到空空的客栈。城堡已出
售;百叶窗松散、凌乱。——神甫想必已拿走了教堂的
钥匙。——公园四周,守卫的住所已空无一人,篱笆高
耸,只见颤动的树尖。况且里面也没什么景致。
草原延伸到没有公鸡,没有铁砧的乡村。拉开闸门。
噢!基督受难的荒野,沙漠上的磨坊,群岛与草垛!
神奇的花朵嗡嗡作响,斜坡摇晃。传说中的野兽优
雅地游走。乌云堆积在热泪汇聚的永恒海空。
Ⅲ
林中有一只鸟,它的歌声使你驻足,使你脸红。
有一口钟从不鸣响。
有一片沼泽藏着白野兽的洞。
有一座教堂沉落又升起一片湖泊。
有一辆被弃的小车披着饰带,顺着林间小路滑落。
有一群装扮好的小演员穿过丛林边缘的大路。
有一个结局:当你饥渴,便有人将你驱逐。
Ⅳ
我是那圣徒,在空地上祈祷——就像温顺的动物埋
头吃草,直到巴勒斯坦海滨。
我是那智者,坐在阴暗的椅子上。树枝和雨点,投
在书房的窗上。
我是那行旅者,走在密林间的大路上;水闸的喧哗,
覆盖了我的脚步。我长久地凝望着落日倾泻的忧郁金流。
我会是一个弃儿,被抛在茫茫沧海的堤岸;或是一
位赶车的小马夫,额头碰到苍天。
小路崎岖,山岗覆盖着灌木。空气凝固。飞鸟与清
泉远在天边!再往前走,想必就到了世界尽头。
ⅴ
最终,租给我一间坟墓吧,用石灰涂白,镶一道凸
出的水泥线,——深藏地下。
我静伏案前,灯光映照着我痴痴重读的报纸和乏味
的书籍。
我的地下沙龙的头顶有一片辽阔的间距,房屋像植
物一样生长,雾锁重楼。污泥黑红,魔幻的城市,无尽
的夜色!
低处滴水,四周惟有土地的厚重。或许是天渊、火
井?或许是月亮与彗星,海洋和神话在此相逢?
苦涩之时,我想象着蓝宝石与金属球。我是沉默的
主人。为什么在苍穹的一角,会出现一扇灰白的窗口?
(王以培译)
地狱一季
以往,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的生命曾是一场盛宴,在那里,所有的心灵全都敞开,所有的美酒纷纷溢出来。
一天夜晚,我让“美”坐在我的双膝上。——我感到她的苦涩。——我污辱了她。
我拿起武器反抗正义。
我逃离。噢,女巫,苦难,仇恨,我的珍宝托付给你们!
我终于使人类的希望在我的精神中幻灭。我像猛兽一样不声不响地在欢乐之上跳跃,为了掐住希望的咽喉。
我叫来刽子手,为了在临死前咬住他们的枪托。我叫来灾难,为了在沙土和鲜血中窒息。不幸曾是我的上帝。
我倒在淤泥里。我在罪恶的空气中把自己晾干。我疯狂地开玩笑。
春天带给我白痴的狞笑。
可是近来,当我最后一次“走调”,我梦想着追寻那古老盛宴的钥匙,在那里,我也许胃口大开。
仁慈就是这把钥匙。——这灵感证实了我的梦。
“你仍将是一个恶棍……”魔王又大声叫喊,——他给我戴上一顶如此美丽的罂粟花冠。“用你所有的胃口、你的私心和所有深重的罪孽,去赢得死亡。”
啊!我太富有了:——可是亲爱的撒旦,我请求您不要怒目而视!我知道您是不喜欢作家描写或是教训人的;在几份小小的怯懦产生之前,我这个下地狱的人从我的手记中为您撕下这可憎的几页。
这是一册兰波亲笔题赠给魏尔伦的诗集,其中还有一段流传至今的轶闻。1873年7月10日,兰波和魏尔伦在布鲁塞尔一家旅店发生争执。兰波忿然起身离去,魏尔伦情急下朝他连放两枪,将对方打伤,自己因此入狱。在牢里,魏尔伦追悔莫及,写下了《屋顶上的天空》一诗,以他忆及的兰波诗句题铭,遂成法国诗坛名篇。至于兰波,他回到法国阿登母亲家中养伤,一晚在顶楼情绪激昂,一气呵成54页的诗作《地狱一季》,文学史上称之为“世纪性的诗艺革命”。然而,兰波当时年仅19岁,只能像一些无名之辈那样自费付印了500册,定价一法郎,最后竟然连一本也没能售出。由于付不起印刷费用,作者只能从印刷者处讨要了几册留存,又挥笔在其中一本的扉页上草草写上:“赠给P·魏尔伦”,托人捎至诗友在布鲁塞尔服刑的监狱。可笑的是,比利时当局认为兰波此举是“赞誉侵犯者”,竟将《地狱一季》封面上的作者姓名刮去。兰波传记的作者让-雅克·勒弗莱尔认为,“这册《地狱一季》在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兰波的手稿业已遗失,而他在绝望时又将自己仅存的几册全都烧毁。后来是靠魏尔伦保留的这一册再版,此作才得以流传于世。
魏尔伦能将珍本《地狱一季》保存下来,也是个奇迹。此翁暮年落拓不堪,跟欧也妮·克兰茨和威洛曼娜·布丹两个妓女潦倒相依为命。三人争执时起,每一吵架,二女就抢走魏尔伦的诗稿和存书,威胁要将之毁掉,其中就包括兰波那本《地狱一季》。多亏画家卡萨尔居间调停,孤本才幸免于难。1896年,魏尔伦病故,把书留给了卡萨尔,继而落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外交部长路·巴尔杜手里。巴氏在书上贴上了一个“裸女出井”图像的藏书标签,又觅到兰波《泪》和《清晨遐思》两首诗的手稿,一同珍藏到他1934年10月9日在马赛遇剌身亡。接着,这三件兰波文物在巴黎知名书商彼埃尔·贝莱斯身边放了70年,后来在巴黎德鲁奥一次竞拍中转手,书商从中获利100万欧元。遥想当初,兰波自己为《地狱一季》定的售价仅为一法郎,相比有天渊之别。
兰波的地狱一季
我曾被彩虹罚下地狱,幸福曾是我的灾难,我的忏悔和我的蛆虫:我的生命如此辽阔,以致于不能仅仅献给力与美。
——阿尔图·兰波(ArthurRimbaud)
在最近出版的《兰波作品全集》中我看到冒险家、过去的诗人兰波在1884年,从也门的亚丁港写给家人的信,他说:“我的生活在此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我很快就30岁了(生命的中途!),我已无力在这个世界上徒劳地奔波。”
我想,说这话时兰波一定想起了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的第一段:“就在我们人生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也许他还想起了自己少年时的诗篇,和他在那些辉煌的诗篇中对自己未来的诅咒)。虽然他说错了,那时他不是在“人生的中途”,而是走近尽头了,但他应是无憾的,因为像但丁一样,他走过了地狱并窥见了真理。
1854年出生的法国诗人阿尔图.兰波是现代诗歌史世不二出的天才——这是当代诗人无一否认的。他在十五岁所写的两首名诗《元音》和《醉舟》,不仅实践了波德莱尔“感觉的交响乐”的梦想而成为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重要代表,还因为开创了一种求索于潜意识和幻想的力量的自由诗风,对后来现代诗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成为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同年他在著名的“灵视者书简”中提出的“诗人应该成为灵视者”这一概念,更对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甚至意识流小说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曾在其成名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结尾处暗示自己所受之影响,并向之致敬。
1871年他结识了另一个大诗人魏尔伦,后者深为他的天才吸引,弃妻子和他出走,两人在伦敦、比利时过了两年的同性恋生活。1873年,这段“孽恋”最终因为兰波想回巴黎而被魏尔伦开枪打伤而完结。一个月后,兰波写出了他最杰出的诗篇《地狱一季》,从此封笔,19岁就完成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生涯。
此后发生的事情是不可理喻的,兰波离开法国,到过南欧、北欧、亚洲、非洲,当过荷兰和美国的雇佣兵(很快成为逃兵)、殖民地监工、武器走私贩、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后来在北非、西亚等地呆了12年,“过着世上最悲惨的生活”,但都没有回过法国。直到1891年他的脚上肿瘤恶化他才不得不回法国做截肢手术,但已无济于事,他于年底死去,终年只有37岁。
对于兰波下半生疯狂的行为,有不少解释:有说他是因为爱情的失落的,有说他是因为江郎才尽改而追求世俗幸福的,甚至有直说他就是因为贪婪金钱而做冒险家的。我觉得这些人都不了解兰波,没有从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这一点去理解他。没错,他后来的确赚了好多钱(他在信中说他长期在腰间缠着八公斤重的金法郎!),但他却一边写信回家诉说在蛮荒之地生活的悲惨,一边又为自己编造种种理由不肯回法国——他在亚丁有何幸福可言?就像《史记·项羽记》中所说“富贵而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般不可理喻,这段地狱的日子是不能从一般人的角度去解释的。
兰波有一句诗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引用而广为人知:“生活在他方!”他还有两句诗同样有名,被写在1968年法国学生革命的街垒上:“我愿成为任何人”和“要么一切,要么全无!”。这些诗句和《地狱一季》,是我们理解他下半生的执着与受难的关键。
兰波的早期诗作已经有许多是抒发他对流浪、冒险、自由的向往之情的了,像《醉舟》,第一句就说:“沿着沉沉的河水漂流而下,/我感觉已经没有纤夫引航”,然后就是数十行对奇幻漂流旅程的天马行空式歌唱,他沉醉于行程的意外多变中,又丝毫不想在任何地方逗留——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他方”,审美者对美总是永不满足的,“生活在他方”意味着永远的变迁。他的诗歌形式也与之配合,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呼唤句、祈望句,急速地在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间跳跃着,名词和形容词的流变纷呈令人目不暇给。在“灵视者书简”中他说:“如果它(诗)天生有一种形式,就赋予它形式;如果它本无定型,就任其自流。”——后来,他为他的生命也选择了这样的形式。
在先于《地狱一季》写下的散文诗集《彩图集》(在兰波死前几年才出版)中,兰波首先在文字上实验了他“我愿成为任何人”的狂想。在一出出小戏剧中披着华丽的面具、彩衣轮流上场的角色们:巫师、戏子、杀手、流浪者、国王、精灵等等,都是兰波自己的化身;而在这流动之中他重新审定了世间的美,为之订立了一个灵视者的新标准——就像尼采在哲学中所作的“重估一切价值”,他也在美学中作了。
他还早于尼采12年提出“人是必须超越的”这般的号召,在“灵视者书简”中他已经说:“诗歌将不再与行动同步,而应超前。”“他(诗人)需要坚定的信仰和超人的力量……将成为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丰富的灵魂!”这就像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的伟愿。而在《彩图集》和接着的《地狱一季》中,他为这种超越作出了一次次的实验,并在他日后的生命中去实践——他选择的生活(雇佣兵、武器走私贩、勘探队员等生活)超出常人所想像,他的毅力也超出常人所能承受的。这种疯狂只能理解为他对自我的磨练,和存在主义式的对选择的承担。
真正预示和确立了他的“地狱变”的,是他的绝笔作《地狱一季》。这部分为九章的散文诗集,完整地呈现了一个质问真理者的心路历程:首先他回忆了他是怎样从对美的爱走向对恶的崇拜中去的——这“恶”并非单纯善恶论的恶,而是混杂了青年人的反叛欲和一个绝对主义者的殉难倾向的一种审美状态;然后他幻想他的地狱游记、他的疯狂行径,充满激情,在狂热的背教渎神与纯洁虔诚之间左右摇摆——因之陷入不断的、残酷的自我灵魂的拷问之中,但从他华美灿烂的文字看来,他却又是沉醉于这拷问中的。他从一个女子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爱——他同时充当爱者和被爱者两个角色,他发现当自己去爱的时候,他戴着撒旦与耶稣的双重面具,这分裂却构成了一个天使般神秘的形象或目标。
在关键的一章“文字炼金术”中,他回顾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创造:“我发明了元音的颜色!”“我默写寂静与夜色,记录无可名状的事物。我确定缤纷的幻影。”读者跟随他游历他的幻想,享受感官、欲望的盛宴。在极乐中他透露了他生命的秘密:“我曾被彩虹罚下地狱,幸福曾是我的灾难,我的忏悔和我的蛆虫:我的生命如此辽阔,以致于不能仅仅献给力与美。”这几乎是对他一生的预示。在最后他明白了:“我如今才懂得向美致敬。”——从这里开始,他的沉沦的地狱篇演变成了上升的天堂篇,在后面的篇章中,他批判着平庸的生命并一直升华自身,反叛的力量反而成了它的对立面:“崇敬”的加速推动力,他甚至说:“我对世界的反叛只是一段短暂的苦刑……我们不会失去永恒!”
但在最后一章他又回复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清醒。他质疑天国、救赎:“我受骗了……我用谎言养育了自己。让我们上路。”他的态度就像后来存在主义者的态度:确认自己的存在,在此不幸的存在中夺取存在的意义。他说:“再也别唱赞美诗:坚持走过的每一步。”现实是残酷的,却意味着真实——真理亦应该从中诞生。
诗以后的生命,就是他以生命去实践、延续诗的过程。看看他在生命后期写给家人的信,那才是真正的地狱一季啊,没有一封不嗟叹生命的悲惨的:“我只有在疲惫与贫困的流浪生活中了此残生,而唯一的前景就是在痛苦中死去。”然而在后面他又问:“你认为我能否找到一个愿意和我一同旅行的人?”在他脚疾恶化,写信托家人买药物后,他竟然还问:“像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去军队服役?”他的冒险精神真可谓至死不渝,在他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被截肢,他知道自己已无可救药,却希望能回到北非,死在埃塞俄比亚。但他未能如愿,他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送到码头……”
这座个人的地狱既是命运的诅咒又是人自己的追求和承担。兰波自喻:“我就是盗火者。”《古兰经》里有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创造者的不幸:“他们譬如燃火的人,当火光照亮了他们四周的时候,真主把他们的光明取去,让他们在重重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这里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追求:为了燃火,他们甘愿身处黑暗。但丁《神曲》中的尤利西斯,不是因为用了木马计欺骗而下地狱,而是因为在他的最后航行中看见了他不应看见的神秘之山——真理而下地狱的。然而倒过来讲,能够窥见真理,虽下地狱又何妨呢?
相对于神秘的命运,这一切:诗歌、幻想、冒险也许都是徒劳的,但这徒劳本身就拥有了意义。本雅明曾就理想主义说过:“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谨以此话献给地狱中的尤利西斯、兰波直至切·格瓦拉等盗火者。
生活在别处,人们以为它的发明者是:兰波,但真正最先提出的却是卢梭。
原文:“野蛮人和社会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livewithinhimself),而真正的社会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意见之中(outsideofhimself)。”(《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8页,转引自朱学勤先生《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
朱学勤先生在他的《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的一条注解中说:“此句中文版译文尚未译足原意,可商榷。法文原文是:toujourshorsdelui转译为英文outsideofhimself,转译为中文,似应为“生活在别处”,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法……”
生活在别处!
英文:LifeIsElsewhere
法语:?ivotjejinde
台湾:生活在他方
“生活在别处?ivotjejinde”首先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巴黎狂欢节”里的名言,1968年前,兰波将这句话从嘴里或笔尖创造了出来:1968年,这句话被刷在巴黎大学的围墙上:1968年之后,米兰·昆德拉将它弄得世人皆知!
在红色的城墙上,
将阴森的光线抛向高高的天穹。
在那片野性与皎洁的黑色大陆,
诗人在星光下,
去寻求采集完美的神所撒下的花朵。
诗人
生活在别处,
在沙漠/海洋,
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
洪水的幽魂刚刚消散。
一句被引用至滥俗的“生活在别处”曾在天才的诗人逝世的不久之后,被他的信仰者们刷在巴黎大学的围墙上,日复一日提醒着我们,这个“被缪斯的手触碰过孩子”举世无伦的才华和他那流光溢彩的诗篇。
兰波曾是整整一代法国年青人的偶像。他们说“他是一切文学流派之父”。自由和梦想燃尽了诗人的生命。
天才动荡不安的生命状态,从14岁开始写诗至19岁完成《地狱一季》,兰波似乎过早的结束了他作为诗人的生命。他是横空出世的才华横溢的天才,却也是转瞬即逝的。
“诗人/生活在别处/在沙漠、海洋。”然后他放下笔,去实现他“我要成为任何人”的梦想。非洲、埃塞俄比亚、印度,他是矿场工人兰波,同时,也是殖民地地主兰波、淘金者兰波,唯独不再是诗人兰波。
只记得milankundera说过:“诗人是一种不成熟的生命状态。”
兰波,作为象征派的代表,这个被称作“第一个朋克诗人”,“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一生都在流浪,追求自由的路上颠沛流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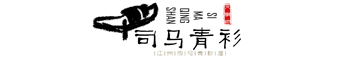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