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妈妈那儿,坐公交车。昏昏欲睡的时候,就听见坐在我后面的那位年轻妈妈,一直在教训儿子。大意就是嫌儿子学习不好,字也写得不好,还就知道玩手机,这次是送他到外婆家劳动改造的。母子俩有问有答,倒也其乐融融。
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很大声的争吵,是司机正在和一个上车的老人说话。原来这等车的老人,看到车门要关上了,下意识地用手去拦,结果手被车门挤到了。好在是有惊无险。老人上了车,坐我身边的女子,起身给老人让座。老人礼貌性地推让着,女子说自己马上下车了,然后她站到车门旁边,做出马上就要下车的样子。
我看到老人的手腕有点青紫,看来挤得还真不轻。老人坐安稳了,就又开始抱怨司机。司机说老人是强行扒车,老人说司机不负责任。眼看两个人就要大吵起来,车上的人都来相劝,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又到了一个站牌,上来六七位乘客,全都是赶闲集的老人。他们坐下之后,就开始很大声地讨论菜价……他们坐车用老年卡,是不收费的。所以,每到这个地方逢集的时候,就有很多老人,大老远地坐了车,就为了来买便宜菜。听着他们一直在讨论,从菜价一直讨论到改革开放之前,又从改革开放之前,说到特朗谱和普京······
一直到这些老人全都下车了,那个让座的女子依然在车门边站着。半旧的黑色平跟鞋,鞋底上沾着一些泥土;黑色带白花的长裙,一直垂到脚面,外面罩了一件枣红色线衣。栗色的头发高高地盘起,淡漠素净的眉眼,优雅娴静的神态。她只淡淡地站在那儿,却显得与车上的人,那么格格不入。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后面响起一声炸雷:
“我说让我妈过十分钟来接我,她怎么还没出发?你让我妈接电话!我说你让我妈接电话……”
满车的人都被吓到了,一起看向那个女子。
那女子穿豆绿色连衣裙,戴一条细细的的金项链,棕红色的卷发,随意地挽成一个发髻。细眉杏眼,淡淡的妆容,指甲明显得修过,涂着黑色的指甲油。她一边很大声地打电话,一边抛出很窘迫的眼神。
那女子终于打完电话,收起手机的那一刻,她很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我爸爸耳背,每次打电话都要这么喊,他才能听到。”
大家全部释然,我也从心里,把她的形象重新给了一个定位。没有人愿意粗鲁,就像没有人愿意贫穷一样。但是无论是谁,有一位耳背的父亲,打电话肯定都是要喊的。
下了车,转乘另一趟公交,还好,车上居然有空调还有座位!
盛夏的时光,好像就是绿树浓阴,就是阳光灿烂。刚刚收割后的麦田,一望无际,水稻的秧苗还在苗圃里长着,绿油油地一片连着一片。荷花已经零星地开了,田田的荷叶,随风舞动,好像自带着万种风情。
想起女儿们还小的时候,暑假来妈妈这儿小住,撑船打莲蓬是我们每年的必修课。撑一条小船,穿行在密密的荷叶下,那感觉倒像钻进无边的森林里。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看看荷花打打莲蓬,那时候觉得那些傍河而居的人家,真是太幸福了,无论阴晴早晚,整个夏天天天都能与荷相伴。
只是,看似诗意的生活,却也一样充满艰辛。
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走着路过一大片荷田。荷农正在荷田里拔草,满腿的泥浆,满脸的汗水,双脚踩在满是烂泥的荷田里,每走一步都很困难。
因为荷田里不能打除草剂,除草全部依靠人工。那么大一片荷田,一眼望不到边,却连一棵树都没有,人整个曝晒在阳光下,就是武装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种稻田和种荷田的人,皮肤一般都特别黑。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但愿我们,都只看到生命的华美!
文丨宗风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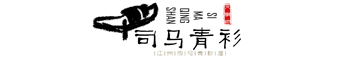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金销藕叶希
旧时天气旧时衣,
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