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香椿树的叶子落尽了,冬天就真的来了。只是,喜鹊的叫声,依然欢快,麻雀的叫声,依然吵杂,鸽群扇动翅膀飞翔的声音,依然震撼……
夜里又做梦了,梦到老家的小枣树上,还有一颗枣。想吃还够不着,打下来还怕找不到。不打下来,还馋得慌……犹豫着,仰望着,纠结着就醒了。
然后就想到,那棵小枣树的旁边,有一条小路。那小路南北走向,窄小得仅容一个人通过。路的左边是邻居家西屋的后墙,右边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榆树。那榆树有碗口粗细,榆树外边,是邻居家很陡的宅基的下坡,坡下面是一排高大粗壮的杨树……
每天,都要踩着那条小路,去井边打水。小小的我挑着扁担,不知从上面走过多少次。先是上坡,接着是下坡,然后走到取水的井边打水。阔大的井口,粗重的井绳,湿漉漉的井台,稳稳当当被拉上来的水桶……
由于杠杆的作用,那水桶出了井口,必须及时抓住,不然……不然会怎样呢?
对啊,不然会怎样呢?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试过,因为每次都很及时地抓住了。有时候去的巧,正好有大人在打水。他们会先把我的水桶灌满,然后,看着我挑起扁担……
那时候,一个村子才有一口吃水的井。石头砌的井台,经过长年累月的踩踏,已经变得十分光滑。井口一米见方,井壁上长满青苔。站在井口的西北角,拉着井绳打水。小小的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也从来没想过,万一掉进那口大水井里,是什么后果……
为什么每次做梦,几乎都梦到童年,梦到老家?离开老家那么多年了,老家也早就没有了原来的影子。为什么梦里的老家,却依然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那一夜做梦,梦到生产队的菜园子了。那儿早就划成了宅基地,盖起了一排排的砖瓦房。可我梦中的菜园子,却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低矮的围墙,破旧的篱笆,古老的水车,蒙着眼睛拉水车的毛驴,总是长满青草的、弯弯曲曲的水沟……
有时候觉得,人会做梦,真是太神奇了!大概也只有在梦中,才能把现在的人物和过去的场景重叠在一起,给你一种真实、虚幻又迷茫的穿越之感。
小时候每到冬天,家家户户都睡得很早。因为冷,也因为没什么好玩的。但是,每次睡到半夜,必然听到那个没有妈妈的孩子,高一声低一声地,沿着长街哭喊他爸爸……
凄厉的哭喊声,总是近了又远了,远了又近了,有时候,一夜要来来回回好几次。
他家在村子的最西北角,三间低矮的土屋,没有院墙,也没有大门。他妈妈疯了跑了,他爸爸迷恋赌博,总是在他睡着之后,偷偷跑出去赌钱。他睡醒看到爸爸不在,就开始沿着长街拖长了声音,一遍一遍地叫喊。几乎每夜都听着他的哭喊声,怀着满心的不安睡去……
从来不知道,那孩子是不是每次都找到了他爸爸;从来不知道,那些漫漫长夜,那孩子都是怎么度过的;也从来不知道,当这个没妈妈的孩子,在这边声声哀号的时候,那个没有了孩子的妈妈,心里又是怎样的煎熬!
那时候的人很穷,似乎也很冷漠。
记得有一个男人打他老婆,东西两庄的人都来看热闹。人越多那男人就越来劲儿,好像对他来说,打老婆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也好像他的老婆根本就不是人……
为什么那么多看热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过去劝解呢?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打他老婆呢?
后来,他老婆终于被他打跑了,他自己孤身一人带着年纪幼小的儿子,潦倒度日。
我一直不能理解,人都穷成那样了,为什么还有闲心去赌、他拿什么赌;一样生而为人,那个男人,为什么那样狠命地打他的女人?虎毒不食子,那么冷的天,他怎么忍心把他那么小的孩子,独自一人留在家里?
忽然就想起来了,这个打老婆的男人,就是那个孩子的爸爸。他妈妈到底是被他爸爸打跑了呢?还是自己疯了跑掉了呢?真的记不起来了。
这事儿当然无从考察,也无须考察。中国有个成语,叫自作自受。觉得就这一个四字成语,已经胜过所有的因果、所有的佛陀……
作者:宗风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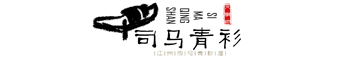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