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男人女人,喜欢你,你就是宝,不喜欢你,你就是草。女人是宝是草,取决于她托付的男人,男人是草是宝取决于他喜欢的女人。托付错了可能人生就毁了,喜欢对了必定开开心心心一辈子,托付和喜欢与长相财富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心应该是爱。 一个女人,年轻时长得很漂亮,是县文工团的台柱子,就是市里的大照相馆都放着她的大幅着彩照片,追她的、介绍的怎么说也应该有一个加强排吧,然而她就跟团里的一个师兄对上了眼,对其情有独钟,师兄那时候就好几口酒,以她的阅历无论如何看不到这事对未来生活是有着极其重大影响的。谁的劝解反对都不行,像祝英台,像兰花花、像李香香,投河上吊生拉活扯也必须在一起。 结婚后过了极其短暂的一段甜蜜日子,后来文工团就垮了,鸟兽散后男人的酒量却由二两变成了半斤,脾气也一天天大起来,女人刚开始是手、身上,闺蜜才看得到的清淤,再后来就是头发鸡窝乱、脸上青一团紫一块,有时还有血痂。当然所有的家务活习惯成自然照例是女人全场包,外面还得摆个摊养家活口,毕竟已生了一个儿子,他总得吃喝拉撒。 女人很快失了鲜艳,失了血色,衣服穿得也没有过去一半立整了,门襟前经常油光光的,扣子似乎也缺了两颗。那些眼睁睁看着女人异色的男人们,一些人说她男人这辈子是来找她收账的,更多男人内心里是一声叹息:暴殄天物啊! 女人生意倒是出奇的好,人们能够帮她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这个女人是她的远房表姐,她和他斜靠在沙发上,他握着她的手听她娓娓述来,她吐气如兰,手温暖绵软。 他们没见面已有二十多年了,他知道,面前的女人已不再年轻了,应该快五十岁了吧。那么,女人讲这个事意味着什么呢,他想起他认识她的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年轻得不谙世事,那时候,她像山野的花自由奔放的绽放着,美丽、鲜活,嫩的若清晨的露珠。在那个流行高仓健、杨在葆的年代,一米七以下都是三等残废,矮小就是丑陋,他哪里会是她园子的菜? 就那样,他和她偶尔校园的几回相遇,他思着念着回味着深刻着,她匆匆而过着无动于衷着,他把她刻在了心里,她对他几一无所知。 年轻时浪漫人生的想法在严苛的现实生活里,会无情无奈的展现出它动人的俗不可耐:他结婚,生儿育女,然后离婚、再婚、再离婚,然后麻木不仁的过着到死不活的日子;她也是结婚,生儿育女,然后离婚、再婚、再准备离婚,习惯流产般的过着没名没堂的生活。生活过到这种份上其实就已是相当乏味了,按人活八十岁计,他们大半辈子已经走过了,但这种伤心伤身的生活让他们哪里又活得过八十岁? 过尽千帆,于是,他们走着走着就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 起初,他一直想像女人的手应该很温暖,像初春的暖阳,握着她的手,千万条金绒线在编织在缠绕。果然,女人的手温润绵柔,没有什么沧桑的枯干粗粝,他就想,这些年她过得并不惬意,那么她又是怎么打理保养这双纤纤玉手的呢。 他觉得幸福就这样随风潜入夜来到了身边,他已经等待了几十年,心似乎有些麻木,激情唤醒时竟然有些慌张,他一遍一遍的在她的耳畔呢喃,声音弱得好像只有她的心才听得见: 好柔软的女人呀,好美好的女人呀!你哪里会有硬的心肠,除非你等待、期盼得太久,心变成了斑斓的玛瑙。 她的头发、脸颊,到耳垂、脖颈、胸腹,无不温软。她的乳房不大,盈盈一握,屁股精巧光滑,髋骨却较大,像个还在生长的姑娘。 窗外暮霭沉沉静寂无声,屋内气喘吁吁娇喘连连。 那柔若无骨的手臂又伸过来了。 •••••• 那晚,他们整夜几乎未睡,但他们仅做了一次爱,久违的幸福洋溢在身心,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微笑着看着彼此,时而给对方掖掖被子。 是啊,已是深秋,天毕竟有些凉了。 上午九点多他被女人唤醒起床时,女人已经把早饭摆在桌上。饭是不稀不稠的绿豆稀饭,精致的瓷碗放在精巧的白瓷盘上,白瓷盘的边上立放着一枚熟鸡蛋,一个碗里放着切了的馒头片,二个小碟里分别是油腐乳和榨菜,竹筷整齐的放在旁边的餐巾纸上,桌子对面是女人的,饭少点,依然显示出一种对称的美。头上的灯是暖色的,女人双手操在胸前,安静优雅的等着,等着他入座就餐。 搞得好复杂啊!他不由得慨叹。 吃完饭,女人不紧不慢的收碗筷和碟子,绝不让他插手;他也不消停,屁颠屁颠的跟在女人的后面,看女人有条不紊的忙碌着:碗筷碟子洗完了,女人会用一张洁白的方巾仔细的擦拭,绝不弄得水流水淌的,碗筷碟子优雅地在女人的手里婆娑着,它们像是珍贵的银器受到女主人特别的照顾。 陡然,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法国女人着高跟鞋、挎着精致的坤包摇摇曳曳的走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情景。 女人着一件小碎花的睡裙,上身套了一件精巧的马甲,身材是那么的纤细、那么的匀称。女人躬着腰在刷洗着昨晚他泡澡后未清洗的浴缸——他这辈子除了在酒店的桑拿泳池泡过澡外,就从来没有在家里泡过澡,更别说享受一个女人温软双手全身上下的洗涮,他回想昨晚从浴缸里跨出来那一刻,觉自己有点恍恍惚惚飘飘欲仙身轻如燕的感觉,当时他没有立稳,还是女人扶了他一把。当他穿上女人给他准备好的睡衣后,酸楚、感动、幸福就像三颗钢珠在百感交集的心头跳来跳去。 浴缸刷洗完,女人依然躬着,她在给他搓洗昨晚换下来的内衣裤,卫生间的门没有关,他坐在客厅里看着女人显得单薄的身子,他莫名其妙的想到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熟语,难道这才是生活?过去几十年都白过了? 女人是必须男人宠的,女人受宠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你的女人,其实可能并非你的女人——爱她才是你的女人,不爱了就是别人的女人。爱着她是宝,不爱她是草。就算对别的男人坏得情何以堪,她也会为你固守一份善良和柔情。 他看电视,女人就在铮亮的木地板上随着中央三台的音乐,近在咫尺的翩翩起舞,就像灯影里摇曳的梦。举手投足都显示着她的功底,毕竟过去是艺术队的人啊,那份曼妙依然能够看到她的年青。 女人有时会给他撒娇的,即便所谓老了的女人,她在心仪的男人面前也会放嗲的。这不,女人一会跳一会唱,一会轻盈的滑在他的大腿上坐得若有若无的、还揽住他的脖颈,一会惊鸿一瞥的给他一个亲吻、拉他起来与她共舞,还会像小女生一般嗲一句:我要你一起来嘛。 真是言已尽而味无穷,难道这就是天真,就是真实? •••••• 那花瓣是一种淡雅的红,又带着润泽的温厚,令人想舔一舔,又令人想轻吮轻吸,她瓣上温红的线条丝丝缕缕,似缓缓流淌的春叶上的珠泪,瓣上轻柔嵌着的肉色点缀着零星的黑点,那黑又不是纯黑,而带着黑郁金香的那种纤巧和飘逸。整个花朵盛开着,清清爽爽蝴蝶翩翩起舞在雪白丰腴的腿股间,修剪整齐的黑亮的草成为花朵天然的烘托物,使之更加娇艳欲滴。 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吗? 她那种举重若轻的不靠谱,那种欲说还休的慵懒,那份随性和自然,那份从容与洒脱,无不令他心醉神驰。 想握着她的手,绵软温润,轻轻地摩挲她们。 这么些年,原来他虚虚空空讨着日子,但似乎又不是那种空虚,是那种心空空如也、无依无靠,想停留想驻足,但好像又回头无岸,灯火阑珊处阒无一人。 难道这就是他在纵里寻的千百度? 他说话从此变得和风细雨,没有脾气了,是女人的美好润泽了他,这对他的肝病有很大好处的。他终究明白了这个女人才是他的心头肉,所以他告诉她只一句话:可发气,别生气,别怄气。 他们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长,但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好好心疼女人一回,他时时记起女人说的:总有人会对我不忍。他觉得他的心在和女人在一起后也变得柔软美好起来了,像春潮冲刷的江堤。 此时此刻,月色皎洁,好想拥她入怀,看她恬静安详的面容,嗅她柔和均匀的呼吸,心中的柔情一江春水般漫过,再漫过•••••• 这块荒芜许久的田地,是她种上了柔软、温馨、甜蜜、幸福,对他而言,她的美、她的好又怎几个词语能够言尽? 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被供在寺庙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 入世太深,哪里又能看淡一切。他感觉这单薄的女人就像琼英卓玛天籁的吟唱,是来渡他的,是来对他临终关怀的,只不过这种临终关怀的时间长了些而已。 阿弥陀佛!
文/废墟上的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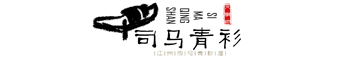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