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黑槐花开时,满地落青黄。黑槐的花比洋槐的小,颜色也偏青,还爱落,树下地上都是它的碎花。花味也特别,青涩涩的苦,轻微微的香。
从前,大门外,左手边有棵老槐树,寂静地立着,有年岁了。记忆里它永远都是那样:合搂粗的树干有两米多高,树皮粗糙,树冠大伞状,撒下的阴凉遮满那片胡同,有许多褐色枯枝掺杂在稠密的绿叶间。树下有个大石臼,邻居们常来树下摧大盐,摧粉条,摧辣椒面,花椒面等。旁边还有一块青石,溜光溜光的青石,是大家说话闲聊,端碗吃饭的热闹地儿。母亲做好晚饭,穿一身汗湿的衣服来青石上坐一会儿,凉快凉快。父亲干完地里活回家,带着满脊背的疲劳坐树下抽根旱烟,然后把短短的烟把子在青石板上捻灭,捻出一个黑圈。我偎在父亲身边,或者学他卷纸烟,或者扑打父亲吐出来的烟圈,或者爬到父亲背上,唱背星星背月亮。家人劳动的辛苦缠绕着吐出的烟圈,消散在老槐树的枝叶间,消散在满是烟火味的老胡同。
那棵老槐树,那块青石板也是我和伙伴们的快乐地儿。我们可以在青石上玩泥巴,走四棋,抓石子儿,玩沙包。还可以和伙伴们在槐树上爬来爬去,逮只水牛(昆虫的一种)用细线栓了云着它飞,摘片槐叶对折后放嘴边,比谁吹的响。槐花开时,花瓣落满地,到了秋天满树的槐连豆可以摘下煮吃。槐连豆成熟时,一串串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晶莹如翡翠。熟到一定程度,母亲喊我们拿着绑了长杆子的镰刀,削下一穗穗的槐连豆,去掉外皮,放清水里泡,一遍两遍三遍的,直到盆里的黑墨色水变清为止。然后捞出,放在大石臼里用兑头轻磕,挤出硬硬的核丢掉,再用清水淘出软软果肉,放和面盆里,加上盐,大料等腌渍一会,用地锅,烧大火煮熟。筋道,润滑,爽口的槐连豆就可以吃了(是果肉,不是硬核)。现在想来,小时候能入口的东西仿佛都是最好吃的。那豆肉是苦味还是酸味,如今已经没有了记忆,只是感觉滑溜溜,黏糊糊。如今若再做来吃,未必能入口下咽。
后来,据说槐米能入药,还能做颜料,有人到村里来买。十里八村的黑槐树就成了大家眼里的宝贝。槐米半开时,摘下,放毒毒的太阳下,一两天就晒得焦干,泛黄,散发出特有的气味。晒好的槐米放在不透气的熟料袋里等贩子们来收购。一棵不多大的树结的槐米能卖二三十块钱,这对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额外进项。于是村里的凡是能骑车出门的大人们都带上杆子镰刀遛村串巷买槐米,骑远的能到鱼台地,济宁地。发现谁家的槐米树,买者大多是估摸着十块八块地包下来,轻轻地削下槐米穗,装袋,付钱,再去寻找下一棵。幸运者,一天下来能削到两三袋子,满满地堆在自行车的货架子上,披星戴月地驮回家,倒在单子片子上晾着。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再背到庭院或平房屋顶上晒。晒半干的槐米就很容易从花枝上搓下来(也不能晒得过干,一搓会成碎末),用簸萁簸出碎枝花片,再把干净槐米端到太阳下晒干,傍晚就有人来收购。那两年,一到暑假黑槐开花时节,哥就早早带上干粮、镰刀、长竹杆等骑车出门。他骑的远,常是别人去不到的地方,所以他每次都能收回来老多。一家人都忙忙活活的。
最怕碰到阴雨天,削来的槐米不能及时晒干,就会发霉发黑,卖不上价钱。一斤上等干槐米卖到七块八块,一季下来一个劳力也能挣到几百元。当然收干槐米的商贩挣得更多,也有人因这生意发了点财。买卖槐米也就那几年,以后就没这营生了,其中原由不清楚。
又到槐米开花时,满树的青黄花儿在自开自落。夏天没有了槐米交易,秋天也不再煮槐连豆吃了,槐连豆自然干瘪,一直挂在树枝上,挂在冬天的寒冷里。
文丨李艳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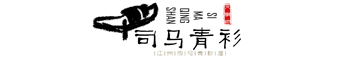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