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中把我送走到了他的怀抱。 我从西校的初中部考到了东校的高中部,意味着我又将唱三年的“皇皇运中”,又将喊三年的“知耻力行”,又将做三年的“舞动青春”。 现在的老班告诉我们说——每一届学生都是一场轮回。是啊,命运的齿轮转啊转,将我从初中抛往了高中部,我却仍然坐在齿轮上不断的道个好,拜个拜,守望着我的运中。 一零年,我踏着秋风步入了运中,那是的它还很丑陋。只有一个狭小的小卖部,却还要接待近百个学生,容不下了就只有排起长长的队,等上好长时间,再扭动灵活的身躯挤进去。进去后,还要使出浑身解数在人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努力伸长胳膊,探着脑袋喊:“阿姨——我要一包小浣熊!”小卖部阿姨迅速从我手中抽走钱,塞,哦不,砸给我一包小浣熊。我必须紧紧地抓住它,因为它极有可能被人群挤掉。最后,我再可以放松地双脚离地任人群夹着把我挤出去,就像夹娃娃机一样。 我挤过了一年。 初二的时候,学校就已焕然一新了,有了新的食堂,新的超市,还有新的“知行堂”。每个星期六,像我这种无聊透顶的人便可以拿着五块钱去“知行堂”的小放映幕前看一场电影,和组团的小伙伴们愉快的度过一下午。 那时我们大了一岁,胆子大了一节,跟老师也亲热了许多。会和老师谈心,会多愁善感地写些悲情文。再后来,老板就严令禁止——不准看郭敬明的小说——他的文,太悲。我却依然像宝一样捧着他的书,眼眶湿了就擦,擦了又湿。直至现在,也会时不时带些感伤情调,想起他的文,她的脸,她的话。 我吊吊着过了一年。 初三时,我没有时间去嘻哈了。只记得那个时候自己特别像个怨妇——怎么还不放假啊?作业这么多,要死啦!初一初二的小孩烦死了,大中午的闹哪样儿啊...... 我吐了一年的槽。 直至毕业,我才闭了嘴,转过身,重新看一遍校园。听着从《兰花草》到《跟着感觉走》;听着上一届的学长学姐骂我们没素质,我们再骂下一届的没素质;看着自己的身影自早操铃开始响时从宿舍五楼冲到了操场后,铃还没有停;看着老师我们并肩而行。 而现在,不一样了。 高中不需要跑早操了,而且我也没有信心在宿舍楼与操场相隔甚远的情况下进行冲刺跑。 不过,我还在运中,还在。我的小伙伴们还在。 高一的我穿上了另一身校服,一天一天的看着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度过,仿佛我仍在“运中”。可是讲台上的脸,神情已经找不到一丝曾经的影子了,似乎这在告诉我——把握住现在,爱上现在,把曾经放在心中,永远为它留一个地方。 我努力让自己爱上现在,让我自己时刻弯起嘴角,对它笑。 命运的齿轮又开始转动,望着消失了的前一个齿轮,我调整好坐姿,最后一次伸出手,向它道谢,致敬,再见。 走在下午吃饭时间空无一人的一楼走廊上,安静的享受清新空气和静谧的小时光。我为自己发现这一处宝地而欣喜,真想唤它一声——阿静,我在这里第一个爱上的地方。 同名不同地,同人不同情。 同情不同人,同心不同爱。 两场轮回。 一场情。
文/青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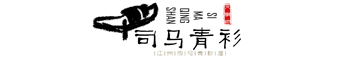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