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腾格里大漠的入口处有个集镇叫冰草湾,,由于连年的兵祸在能够通过大漠的官道上,经常有一些散兵游勇作乱,他们比强盗更凶残,比土匪更强悍,因为他们曾经是军队,有着很强的攻防能力。所以,许多商人情愿走沙漠绕行穿过也不愿意走官道,走沙漠需要骆驼、需要向导、需要保镖、所以在驼队进入沙漠之前要储备干粮、水、草料、和帐蓬冰草湾上的居民就是靠着做点驼队的生意来维持生计。
任璇儿来到冰草湾天已经中午了,他走进一家招牌被油烟熏得乌七八黑的‘老陈酒馆’堂屋的大厅里烧着一个大火炉,屋里四处飘散着‘五香牛肉’的香味,任璇儿向掌柜的要一了二块烙饼和一斤卤牛肉,他一边吃着一边喝掌柜的聊了起来:“大叔,我想请问您一下啊,我想要穿过这个沙漠到北边的草原去,应该怎么走啊?”
掌柜的是个胖子,好象开饭馆的都是胖子,他围着一个可以用刀刮下油来的围裙,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他看了看任璇儿:“小兄弟,你一个人要穿过这沙漠啊?”
任璇儿边吃边点了点头:“嗯,是啊!”
“你既没骆驼、又没向导、这腾格里沙漠方圆好几百里地,你就这么一个人穿过吗?”
掌柜的直摇脑袋,下面的话没好意思说出来,任璇儿大概也听出来了,在这个初冬的天气,一个人,既没骆驼、又没向导根本不可能穿过这个沙漠,几乎就是在找死,一点机会都没有。
任璇儿也沉默了,半晌又和掌柜的说道:“大叔,是奉了恩师之命一定要穿过沙漠去找我一个师伯,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任璇儿本来长得就讨人喜欢,加上他大叔长大叔短的叫着,在他坚持付了一锭沉甸甸的银子任为酒菜之资以后,那个掌柜的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北方人性格本就比较豪爽,掌柜的决定帮助任璇儿,他想了想对任璇儿说:“我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个回子,(这儿指的是回族人)别人都叫他回老爹,就住在巷子西边的破瓦房里面,他是我们镇上最好的向导,你就是你是饭馆里的老陈介绍你来的,看看他那儿最近有没有驼队要过沙漠的?”
任璇儿连声道谢,告别了饭馆的陈掌柜,出门向西而去。
在一个和比破庙好不到哪儿去的房子门前,任璇儿看见一个须发花白戴着一个白帽子的老人在劈柴。
任璇儿叫了一声:“老伯,请问您一下,这儿有个叫回老爹的吗?”
老人直起腰来,任璇儿看见他那榆树皮一样黝黑的脸庞笑了一笑,他露出两排发黄的牙齿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任璇儿从他手里拿过柴刀:“老爹,我来帮你,是饭馆的陈大叔叫我来找你的。”
任璇儿一边劈柴一边和老人闲聊着,任璇儿柴刀从木头的上面下去到木头的分成两半木头连晃也不晃,任璇儿劈出来的柴几乎一样粗细,老人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劈柴,半天才冒出一句:“小伙子,你是个好把式啊!”
任璇儿知道‘好把式’是干活一把好手的意思,他谦逊笑了笑:“老爹我也是穷苦人嘛!”
一老一少越聊越投机,回老爹越发喜欢眼前这个小伙子了,他心里在想,要是我当年结婚了现在孩子也该和他一般年纪了,他‘嗯’了一声,说道:“孩子,你在我这儿住两天,我有预感,这两天就会有人找我带路,而且是个大主顾,因为,走沙漠的镖都比较小心,到时人家要问你,你就说是我干儿子吧!”
“哎,老爹!”任璇儿高兴得答应着。
现在城市的年青人可能不知道土墙是怎么回事,在那个年代农村盖房子都是用泥土和匀之后打成墙,建筑工人以前一直叫泥瓦工就是这样的由来,这样的墙也有好处,就是冬暖夏凉但是不好地方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开裂,里面还会住蛇,任璇儿住了两天看到回老爹的墙上好多裂缝,他决定替回老爹补一补这土墙,这天,他一大早就和了点泥巴,先用水把土墙湿润再用和好的泥巴填进去、又把表面和里面泥平。他刚把墙补好,人还站在梯子上没有下来,听见有人问他:“这儿有个叫回老爹的吗?”
任璇儿一听乐了:“哟,这台词我前两天刚说过啊,”
任璇儿低头一看两个武师模样的人站在门口,后面跟着两个藏族服饰的女子。一个戴着面沙,一个作下人打扮。
任璇儿朝屋里喊了一声:“老爹,来客人啦!”
回老爹把几人让进屋内,任璇儿也洗了洗手跟了进来。这时,他听见那个戴面沙的女子问回老爹:“带我们过沙漠到‘查汗池’这个地方要多少银子?”
任璇儿此时才发现这个女子长得非常漂亮,高挑的身材、纤细的腰肢、白嫩的皮肤、大大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在这个大漠贫瘠之地这样的女子无疑是一道风景,难得一见的。
回老爹说:“往日五十两就够了,可眼下这个天气你们得多加点。”
那女子倒是非常的爽快:“我们这趟是有风险的,给你一百两吧!我再问你个事,你有没有听说过‘黑旋风’这个名字?”那女子嗓音清脆悦耳,但是汉话好象说得不大流利,语调有点生硬。
回老爹说:“听倒是听过,他们是近几年来沙漠里最凶悍的一马贼,全部是黑衣黑马、黑巾蒙面、号称‘黑旋风’但是我从没有见过。
那女子看了看刚进屋的任璇儿又问:“他是谁?”
“他是我干儿子,会帮着我照料牲口什么的”
这时,任璇儿看见这女子手里面拿着一把很长的弯刀。
这时,那个镖师模样的人说话了:“回老爹,我是镇远镖局的镖头赵长贵,许多零碎琐事还要麻烦您老人家了”
回老爹说:“赵镖头放心好了,我们明天替你购齐一切用品”
那位藏族姑娘从怀里掏出来两封银子放在桌上说:“这里二百两银子,一半给你,一半是用来买东西,办妥了到如归客栈找我们。”
那女子说完一行人飘然而去,任璇儿闻着那姑娘身上留下淡淡的兰花香气。
回老爹对任璇儿说:“孩子,我说的不错吧?遇到贵人了。”他得了那么多银子,乐得眉开眼笑。
任璇儿沉思了一会儿,问:“老爹,那个叫赵长贵的是什么人?”
回老爹边把银子放入怀中边对任璇儿说:“他是甘州府镇远镖局的教头,外号‘赵一刀’是镇远镖局的第一高手,这次连他都出动了看来这趟镖不小啊!”
任璇儿道:“恐怕这趟活不好做啊?老爹?您这个向导也要承担不少的风险的,您看这不是多给您那么多的银子嘛,哪有好好的多给那么多银子的,要不他们的货很贵重,要不就是他们知道会有人算计他们,连第一镖头都出动了,还请最好的向导,这次,有点问题啊?”
回老爹道:“唉,孩子,现在这个世道,做我们这个行业到哪儿没风险啊,过一天算一天吧!你是不是怕了,孩子?”
任璇儿笑了笑。
两天后驼队出发了,前面是四名武师开道,赵长贵和那两个藏族女子走在中间,镖车四角护镖的是镇远镖局的四大金刚:‘夺命刀’韩松;‘追魂剑’秦峰;‘如意棍’常虎;‘锁喉枪’杜铁山,后面是八名趟子手,全是一流的好手,最后面的那个脸色阴沉的黑衣人叫‘黑班克’是镇远镖局请来的镖师,据说在不久前救过赵长贵,功夫还蛮不错的。
任璇儿跟在队伍后面,方便照应牲口。
驼队走出效外时,任璇儿策马来到回老爹跟前:“老爹,还要我做点什么啊?”
“没什么事了,孩子,你知道我攒够了钱做什么吗?”
任璇儿摇了摇头。
“我要在这里修一个亭子”
“修亭子,为什么?”
回老爹望着远方,过了许久才幽幽地说:“因为在许多年前,我答应过一个姑娘,说我会在城外十里的地方有颗小树下等她,可这颗小树却让人给弄没了,她也不知走了多远,一直走到没有回来,后来,我就发誓等到我有钱了我一定在这地方修一个亭子,上面刻上她的名字,让她不再迷路,让她记得找回来…..”
任璇儿知道那一定是老爹一生情感的寄托,他不敢问结果,他也早已猜到那个姑娘可能那次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看见老爹眼中流下两行混浊的老泪。
任璇儿一阵心酸,他对老爹说道:“老爹,我给你唱两句吧!”
在中国大西北地区很流行吊嗓子,现在说法叫信天游,隔个山沟拉句话,对着大山唱两句情歌,以抒情怀,既能表情又能达意,从汉唐朝后许多人还喜欢嘬口长啸以示清高,象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也就是应此而生。
任璇儿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哎…..天上的月亮啊,银光光的亮,
就像那我个的那个小妹妹眼睛哟水格汪汪?
黑漆漆夜晚哟,黑黝黝的山哪!
想死的人的那个小妹妹,你走的哪道山?
情哥哥,我找你跑断了了腿。
大半夜的做梦唉心呀慌慌,
找遍了山沟沟,没见那个人哪,
叫一声:“我的妹妹哟,你在哪个地方?
青溜溜草啊,红溜溜的花,
情妹妹的那个小脸那个呀象彩霞。
弯弯的月儿呀,天空空的挂,
流浪的家的人儿,何时能回家……?”
赵长贵从前面掉过头来喊了一句:“小兄弟,嗓子不错啊!”那两个藏族的姑娘也扭过头来,看着任璇儿。
大漠虽然荒凉,可景色尉为奇观,天底下一望无垠的全是黄沙,就象画中的一样,此时正值黄昏,西边一轮红日冉冉下落,真是一付绝美的大漠风情画,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任璇儿看了看天边快要落下的红日,心里算着,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忽然想起陈子昂的两句诗:‘念天地之悠远,独沧然而泪下’心中涌起一股豪壮悲凉之情。
回老爹喊了一声:“大家不要走了,歇一宿明天再赶路,明天再赶一天就到奴儿盖了,过了奴儿盖就是你们要去的查汉池了。”
驼队停了下来,各人忙着搭帐蓬,此时,夕阳快要落山,大地披上了一层金纱,那位藏族姑娘站在夕阳下,金色的阳光洒在她那镶着花边的紫色藏袍上,把她那娇人的身材勾勒得更加美丽,任璇儿看得痴了。姑娘掉过头正好看见任璇儿发呆的样子,她举起马鞭朝任璇儿打去,任璇儿傻了一样,动也不动,姑娘笑了,马鞭轻轻地落在任璇儿头上…..两个人的眼里心中都迸出了异样的火花。
在沙漠里有这么一句话:‘早穿皮袄晚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得就是沙漠中早晚气温相差很大,有点无常,这白天热得象个火炉,晚上却冷的象个冰窑一样了,任璇儿把身上的皮袄毯子裹了裹,身子蜷成一团,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天,驼队又开始出发了,有了第一天的经历,那姑娘好像对任璇儿友好了不少,还主动扔了一大块牛肉干给任璇儿。
驼队在沙漠里缓缓行着,回老爹不时用手搭凉蓬朝前方张望,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叫了起来:“嘿,奴儿盖到了。”众人听到这话朝前看去,果然,前面出现了一块大平坡,周围有许多沙丘把这块平坡象是保护一样的围绕了起来,
赵长贵大声喊道:“兄弟们,注意前面地势奇特,不要中了敌人的暗算。”
任璇儿感觉到有点不对,那么多年刀尖上打滚的生涯,让他有一种野兽的直觉,经验告诉他要出事,他向赵长贵打了个手势,这个是刀客专用的手势,告诉了赵长贵要注意了,驼队慢慢走到平坡中间,忽然四周响起了一片喊杀声,周围尘土飞扬,许多黑衣黑马的蒙面人从沙丘后面冲了过来。
赵长贵大喝一声:“兄弟们,守住镖车,玩命的时候到了。”
场面一片混乱,黑衣人仗着人多势众,一昧强攻,黑衣人挥舞着长刀,叫喊着冲杀不停,镖师们也各拿兵器,奋力拼搏。
任璇儿对回老爹说:“老爹,你在我身后面,不要乱动。”
这时,他看见那个黑班克忽地往后退了两步,前方一阵羽箭响声,一排弩箭射了过来,前面的几名镖师被射中,立刻气绝身亡,看来箭上是涂了剧素。
赵长贵不愧是镇远镖局的第一高手,他以一敌五,他大声呼喝着,一把雁翎刀舞得水泼不进,众镖师也知道这是性命悠关的时刻,谁都不敢分神,劫匪中有个带头的有个黑衣人始终没有动手,他冷冷地站在后面,忽然他甩出一道寒光,“哎哟”一声常虎爱伤,跟着杜铁山也倒下了,这个黑衣人形如鬼魅、招式奇特,他到哪儿哪儿就有镖师倒下。
任璇儿听到回老爹‘啊’了一声,他转脸一看,回老爹脸色发青,任璇儿大吃一惊连声呼唤:“老爹,老爹,你怎么了?”
他用手一摸回老爹的后背,全是鲜血,回老爹后背不知何时被一支弩箭射中了,老人无力的望着任璇儿,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只是嘴动了两下,就带着无限的遗憾、无限的眷恋闭上了眼睛。刹那间,任璇儿心如刀绞,他两只眼睛象是要喷出火来,他狂叫一声,冲到黑衣人跟前,刀光象闪电一样飞出,一声惨叫,那个领头的黑衣人脑袋被任璇儿一刀劈成了两半,任璇儿疯了一样,刀光如匹练般飞舞,他的耳朵里只有惨叫声和刀砍入人体的声音,黑衣人一个个的在他面前倒下,赵长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吃惊地看着任璇儿,任璇儿如虎入羊群一般,没有人能挡住他的刀,他的四周刀光闪烁、血花飞溅,不知过了多久,站着的只有任璇儿、秦峰、韩松、黑班克和那两个藏族姑娘,几匹主人已经战死的马正茫然的站在那儿。任璇儿对赵长贵说:“牵上那几匹马,赶快离开这儿。”任璇儿说这话时,别人感到了一种威严,这种威严不是谁都能学得上的,是长期以来发号施令的人当老大的人才有的一种威严之气,赵长贵问:“这位兄弟,请教一下,您的尊姓大名啊?”
“任璇儿”
“啊,原来是任大侠…..”
任璇儿手一摆:“先把老爹和兄弟们的遗体埋了,离开再说……”
一行七人,在沙漠里疲惫的走着,由于刚才那场惨烈绝伦的恶战,众人已经感到了死亡的逼近,在他们心中把任璇儿当成救命的稻草一切唯他马首是瞻了。
赵长贵对任璇儿说道:“任大侠,我早说听说过‘刀神’这两个字,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年青,对你不敬之处,你不会怪我吧?”
任璇儿摇了摇头,他转过脸问那个藏族姑娘:“姑娘,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送到查汉池去吗?”
藏族的姑娘点了点头,她由以前瞧不上这个毛头小伙子,到有点喜欢,一下子,变成了全部依赖了,还真的点不适应,慢慢用她那生硬的汉语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任璇儿:她叫卓码,是个藏族部落头领的女儿,本来,由于她们在一个山谷中的特殊地理位置,连蒙古人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她们的部落过着与世无争的游牧生活,后来,她们那儿出现了一个‘红衣教‘的组织,他们要卓码的父亲加入他们的红衣教,头领不肯,于是红衣教主就对着卓码的族人施了邪术,那几个被施了邪术的族人回到家中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全部杀死之后又放了一把火把自己也烧死了,从此以后灾难不断,头领没有办法,只好向红衣教主求饶,红衣教主提出一个条件,为了证明他们是真心向佛的,必须要卓码带着这么多的珠宝到查汉池他们的主教寺院班禅寺来朝圣。头领没办法,为了他的族人,只好答应,那个女仆叫了阿美,是从小和卓码一起长大的,她非要陪卓码一起来。任璇儿用敬佩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为了救别人而自己不怕入火坑的姑娘,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美丽的姑娘伟大起来。
这时,秦峰走过来对任璇儿说:“任大侠,水快没了。”
任璇儿接过水袋掂了掂说:“从现在开始,每个人不许多说话,不许小便,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喝水,赵大哥,水袋交给你,你别叫我什么大侠,大家都是兄弟。”
一行人又在沙漠里不知走了多久,赵长贵把水袋递给任璇儿:“任兄弟,就你没有喝水了。”
任璇儿接过水袋看大家都在看着他,他喉头一阵哽咽,他扬起水袋水袋里面只流出一小口水,这时,他忽然觉得那个黑班克眼神有点怪怪的。
一行七人,在沙漠里继续行走,任璇儿只觉得脚步越来越重,头晕晕沉沉的,他忽然脚下一软,几乎站立不住,卓码问:“任大哥,你怎么了?”
“我可能在发热。”任璇儿道。
几个人都围了过来,赵长贵用手试了试任璇儿的额头:“嗯,烧得很厉害,秦峰,你把驼背上的东西丢掉一些,扶任大侠上去。”
太阳毒辣辣地照在任璇儿的身上,任璇儿趴在驼背上,手里紧紧的握住那把叫‘天炽;的黑刀。天渐渐黑了,风又呼呼地刮了起来,由于一天一夜没有喝什么水,任璇儿已经接近昏迷的状态了,.
这时,赵长贵忽然说:“前面好象有房子。”
有房子就有人家了,这就说明他们到沙漠的边缘了,所有人心里都是一阵兴奋,任璇儿心里也是十分的欢喜,他用力的摇了摇脑袋,对赵长贵说:“赵大哥,你先到前面去看一下,我们再进去。”
过了一会儿,赵长贵在前面叫道:“喂,任大侠,你们快来啊,这儿是座破庙。”
“破庙,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哪来的破庙?”任璇儿心中有点疑惑,但是全身象火烫一样,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众人进庙以后,赵长贵把神翕扫了一下,扶着任璇儿躺下,卓码和阿美围着任璇儿坐了下来,眼睛里面充满了担心和忧郁,任璇儿笑了笑,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就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迷迷糊糊中他看见‘回老爹’任璇儿拉着他的手问:“老爹,你怎么在这儿,你没事了吗?”
回老爹慈祥地望着任璇儿:“孩子啊,你今天杀了好多人,对吗,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任璇儿道:“他们杀了你,我为你报仇,再说,我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啊,
回老爹慈祥地说:“听老爹的话不要再杀人了…….。”
这时任璇儿的身边出现了许多满脸是血的人,有魏伦还有许多黑衣人,都是死在他刀下的人,任璇儿看着自己的双手全是殷红殷红的鲜血。他问自己:“我是刽子手吗?我是屠夫吗?我为什么会杀那么多人,我真该死,”刹那间他心中充满了悔恨,这时,他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老和尚正静静地坐在神翕上,任璇儿走过去,跪倒在他面前不停的磕头:“大师,我罪孽深重,求大师超渡,求大师超渡啊!”
老和尚抬起头看着他:“任璇儿,你想出家?”
任璇儿泪流满面,“我愿遁入空门,忏悔思过,从此不再拿刀,归依我佛。”
老和尚轻轻地扶起他:“任璇儿,你所杀之人,全是奸恶之徒,你不杀他们他们不但要杀你还要杀许多无辜之人,你说那应该怎么办啊?”
“那,我没错?”任璇儿一脸疑惑。
“没错,佛在心中,刀在手中,我佛虽然不教人杀戮,但为救他人性命除恶就是行善。老和尚说得斩钉截铁。我还有句话要告诉你,班克在梵语中就是老大的意思,你张开嘴巴我解你病痛。”
任璇儿张开嘴巴,老和尚手一指几滴甘露滴入他口中,烦恶立解,心中有说不出来的舒爽。
“我去了”老和尚说完飘然而去。
“大师,大师,”任璇儿连忙叫道,这时,他忽然听到有人叫他:“任大哥,任大哥,”
任璇儿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卓码在叫他,他自己原来是做了一场梦,他看见卓码正靠在他脸上,两颗大眼睛满是泪花,滴落在他的唇上,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咸咸的。
此时,任璇儿灵台一片清明,烧尽然退了,病也好了,他笑了笑:“别哭了,我没事了。
卓码吃了一惊:“任大哥,你醒了?”
任璇儿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赵长贵连忙过来要扶他,任璇儿朝黑班克招了招手,黑班克带着诧异的表情走了过来,任璇儿身体一斜右腿踹出,一脚把黑班克踹得飞起来,重重地撞到墙上又倒在了地上,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赵长贵吃了一惊问:“任大侠,你这是什么意思?”
任璇儿看着倒在地上的黑班克,他脸冷地像要结冰一样,他把手按在了刀柄上眼中流露出阵阵让人内心发颤的杀意:“我们中间的内鬼就是他”
“赵大哥,我问你,你们是不是刚结识不久?”
“是的”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以前是大户人家的护院镖师”
“昨天晚上,我喝水前,他碰过水袋是不是?”
“嗯,他最后一个喝的水,他还说我身上有血迹。”
任璇儿一步一步的逼进黑班克:“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当时马贼杀上来的时候,别人都往前迎上去,他却在关键时候往后退了几步,因为他早就知道会有一排毒箭射来,二来以他的武功如果说只是一个护院的镖师,不可能活到现在,你看一看活下来人,要不是就红衣教主想要的两人女人,还有就是你们拚命死战的幸存者,因为你们确实是一流的好手,黑衣人虽多却一时杀不了你们,他却毫发无损,这不是一件奇怪的地方吗,再说,他如果真的有那么高的武功怎么会给人去当一名护院的武师?他为什么又要伪装他的武功,而我看见他和黑衣人对阵并没有黑衣人围攻他,他也并没有杀一个黑衣人,答案只有一个,他就是我们中间的奸细,从现在形势来看,他也许就是那个黑旋风了,班克在梵语中就是老大的意思吧?他本来算得很准确是想杀掉你们几个镖师然后夺走财宝,抢走两个姑娘,可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一个我来,他见机不妙,只好继续装佯,和我们混在一起,他见我杀了那些个黑衣人,他恐怕不是我的对手,必须要先把我害死,所以,他选择了下毒,他喝水时故意和赵大哥说话,就是为了引开别人的注意力,好把药粉放在水里,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喝水,我只是嘴唇碰了一下水,可是,他下的毒还是很厉害,我就嘴唇碰了一下还是中了招,还好我任璇儿福大命大,没死在他的毒下,马贼怎么知道卓码要走这条路,镇远镖局要保一趟镖,这样看来也是早有预谋的了,那么所谓的红衣教主和他也是一路的人,只是他接到红衣教主的吩咐并没有打算照他的要求来做,他想自己独吞这些财宝和两个女人,我说是对吗?黑班克,黑老大?
黑班克恨恨地望着任璇儿,眼中满是恶毒之意。
任璇儿脸一象罩了一层寒霜,右手青筋暴出,双目象冷电一样盯着黑班克,黑班克盯着任璇儿的刀,黑黑的刀柄、黑黑的刀鞘、他忽地想起那些死在这柄刀下的黑衣人,和那个被任璇儿一刀劈成两半的假黑旋风,只觉得手足酸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你要杀了我?”
任璇儿摇了摇头:“我不打算杀你,只要你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情,我放过你。我虽然想一刀一刀的杀你,可我还是会说到做到,放了你,希望你相信我的人品。”
“我现在要你告诉我,红衣教主在哪儿设的埋伏,他们有几个人,打算怎么对付赵大哥他们,我问你一句,你不说,我割你一只耳朵,我问你第二句你还是不说,我割你另外一只耳朵,我问你第三句,你要是仍然不说,我就叫你再也做不成男人,我想,你不会认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吧?”
任璇儿抽出黑刀放在黑班克的耳朵上,一字一字地说:“我现在开始问了,红衣教主在哪儿?打算怎么埋伏?他们有几个人?”
黑班克哼了一声。
任璇儿笑了,他慢慢的拉动黑刀,慢慢的把黑班克的耳朵割了下来,因为黑刀真的很快,任璇儿没怎么费劲,黑班克的耳朵就掉了下来,等任璇儿把刀拿开的时候鲜血才喷出来,黑班克杀猪一样的惨叫起来,
任璇儿冷冷地道“看来,你这个黑老大也不怎么样嘛?”
任璇儿等他停了一下,又把刀放在黑班克另一只耳朵上:“黑班克,你不说出来,我们也会找到他们或者说他们也会找到我们的,可是,你却没了好多部件,哈哈,我不杀你,我却让你只有人的一部分活着,你觉得那样是不是活得很有趣味啊?”
黑班克终于让任璇儿的话给攻到内心深处,彻底崩溃了,他发出狼一样嗥叫:“好,我说,你放过我一命,我说,他们九个人在查汉池的班禅寺,打算用摄心术来对付你们”
任璇儿冷冷的看着他。
“向北再走半天就到了”
黑班克说完痛得昏了过去。
任璇儿在他怀里搜了搜,找到了一个磁瓶子,他把磁瓶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放入了怀中,任璇儿吩咐赵长贵道:“赵大哥,把这个黑班克给捆上,就扔在这个破庙中,我说过我不杀他,可他能不能活下来,那就得看他的命好不好了?哈哈!”
秦峰杀了一匹马,虽然,生马血又热又烘,但是为了保命,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喝了一肚子马血。
天一亮,几人就离开了破庙,任璇儿掉过头看着破庙心中在想:“难道真得是佛祖显灵点化与我?”他嘴里反复的念叨着:“佛在心中、刀在手中、除恶就是行善、无佛无我、无我无佛、我即是佛、佛即是我……”当年,任璇儿杀第一个人时一连几晚做恶梦,现在,这么多年来一直纠缠在心里的心结一下解开了,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他朝着破庙虔诚的拜了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心结,任璇儿也不例外,他的心结比谁都要重,因为,杀人必竟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可是他实再是没得选择,他不杀人,别人就杀他,为了生存,他不停的杀人,他不停的用刀,用到最后连他自己心中都有了障碍。现在,这个障碍总算消除了,他心中真的是有‘立地成佛的感觉,因为,他明白了,自己不是在作恶,而是在行善。除恶就是行善,无佛则无我,这也是他自己从自己所学经书知识里面悟到一些东西,通过这件事,他也走出自己的心中的困感!所以,他才朝着破庙虔诚的拜了几拜,他想每个人都会拜佛,与其说是拜佛还不如说是拜自己心中的愿望。
查汉池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集镇,任璇儿一行六人来到了镇上,找了客店住了下来,他们是先狠狠地大吃一顿,再洗个澡,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阳光暖洋洋的照在他们的身上。
中午饭后,几个人来到任璇儿的房间,经过一夜的休整,个个全是精神焕发,任璇儿看了看大家笑了:“我问了问店家,那个班禅寺就是镇北边,我也出去转了一圈子,找到了那个寺,老百姓一直觉得是个魔窟,经常闹鬼,许多进去上香的人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住着几个凶神恶煞一样的红衣喇嘛,你们中间有人不愿意去的吗?”
赵长贵看了看韩松和秦峰两个人,又看了看两位姑娘,韩松道:“任大侠,我们虽然功夫不如你,可和你一样的血性汉子!”
秦峰道:“就算我们不去,你们要是完了,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管他娘的,拚了!“
任璇儿道:“好,你们到院子里来”
几个人跟着任璇儿进入了院内,任璇儿带着他们到了一颗枯死的小树边上。
任璇儿道:“他们说要用摄心术来对付我们,其实所谓什么邪教、邪术啊,我虽然不懂,但是武学一道触类旁通,如果他们真的能控制人的想法他们就不用那么费事的挖墙掏洞的算计别人的,他们无非是用一些声音或者眼神来迷惑别人,我们几个人全部穿上黑衣,扮作黑旋风的人,进庙之后看见那些红衣秃驴们,对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不要看他们的脸,到时候你们就给我猛砍就行了,卓码和阿美断后,发现,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对头就大声音叫唤,打乱他们的干扰,明白吗?”
“好”众人答道。
任璇儿从包里拿出两个牛皮的马甲,扔给卓码和阿美道:“这个虽然抵挡不了强工硬弩,但是可以防普通的暗器,我上午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皮匠,只做了两件,我们男人就不需要了,另外,我有一招刀法,说出来,供大家参照,秦大哥虽然使剑,但是也可以看一看,好吗?”
几人大喜过望,秦松道:“任大侠,人家练武之人对功夫都是十分的保守,可你却不是嘛?”
任璇儿道:“发扬才能光大,不管是什么技能,只有让更多的人来研究它才会不断进步,这刀法也一样,再说了,就算我告诉你了刀法,心法,可你不去苦练,还是没有用的。”
任璇儿道:“你们看好了”他对准院内那颗枯死的小树,手绕出一个弧形,刀光一闪,小树从中间断开,断面光滑平整。
几个人参参悟了半天,也只是似是而非,卓码和阿美更是只学了个动作,至于心法和技巧更是不知所云了。
任璇儿笑了笑:“好了,够了,我想,我们那么多人对付他们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绰绰有余了,领头的由我来收拾,他们的武功不会多高的,不然也用不着找黑旋风这群混蛋来作帮手了。”
任璇儿一行六人换上黑衣,来到了城北的班禅寺,寺院的大门紧闭着,任璇儿用眼神指挥赵长贵从边上不断地拍门环,一会儿出来一个贼眉鼠眼的红衣喇嘛,他刚把门打开一条缝隙,任璇儿飞起来一脚踹在了门上,那个红衣喇嘛被大门重重地撞倒在地上,刚想爬起来只觉得脖子上一凉就一命呜呼了。六人冲到院子中间,看见几个穿着红衣的喇嘛,其中一个个头很高,瘦得象一根麻杆,他的衣服上绣着几朵金花,任璇儿想这个一定就是红衣教主了,只见红衣教主大喝一声,上来几个红喇嘛围住了任璇儿六人,任璇儿数了数连他进门时杀掉的那一个正好九人,任璇儿乐了,这下也省得每个角落去找他们了,任璇儿眯着眼睛看了看,那个子很高的红衣教主瘦得象麻杆一样的身体上穿得那件红袍就象一个木棍上裹着一块红布,空空荡荡,他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任璇儿忽然觉得他的脸长得十分怪异,可又说不出怪在哪儿?任璇儿看了第一眼想看第二眼,看了第二眼想看第三眼,看了第三眼后,任璇儿头脑一片迷糊,象晕了一样,手脚无力想睡觉,
这时,卓码在后面叫道:“任大哥,你怎么了?”
任璇儿心中‘忽’地一下子清醒过来,那个老和尚的话撞钟一样在心里想起‘佛在心中、刀在手中、除恶就是行善、无佛无我、无我无佛、我即是佛、佛即是我……’任璇儿蓦地大喝一声:“杀”
赵长贵等人也正犯迷糊,听他这一喊刹那间清醒过来,拔出兵器杀了过去,庙中顿时刀光血影…...
对着满院的喇嘛的尸体,大家还有些心有余悸,秦峰对任璇儿说道:“任大侠,我刚才听到你喊‘杀’的时候我看你时见你身上有金光闪耀。”
任璇儿笑了起来:“秦大哥,你开玩笑了,我又不是菩萨,哪来的金光啊,哈哈!”
可秦峰心里也很奇怪:“可我却实看见了金光闪烁了啊”
任璇儿道:“我修习的内功是少林派的大法轮功,师父曾经说过,当修行到了一定境界时运功时身上会有金色法轮出现,不知是不是这缘故,只是我的修行恐怕还没到那境界吧?“
众人吃了一惊:“大法轮功,不是已经失传了吗?当年,二百多年前少林派的第一高手,达摩堂首座,无为大师,圆寂以后,这世上最具阳刚之性的大法轮功就此失传,您是从哪儿学来的?”
任璇儿笑了笑,那只是说在少林寺内是没人会了,可有许多曾经打出少林的俗家弟子,就有会的,还有一些成了
千里搭长棚,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朋友是同一段路时一起走的人,现在路要拐弯了,任璇儿要去草原了,别的人,则是要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了,大家心中都有不舍,但是,生活总是那么的无奈。
任璇儿要赶路了,大家不知说什么是好,这么多天的出生入死几人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秦峰、韩松、赵长贵一个个上前抱了抱他。、
“保重”
“保重”
任璇儿对赵长贵说:“赵大哥,可以帮我个忙吗?”
赵长贵道“但有所需,我一定全力以付”
任璇儿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给赵长贵对他说:“帮我在冰草湾郊外十里的地方,就是那天我唱歌的地方,修一个亭子,上面刻上这么几个字‘盼你归来兮’好吗?”
“好,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为了一个老人的愿望,一个带我们走过大半个沙漠却无辜送命的老人,一个曾经阴差阳错让他痛失的一个受人,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这次客死他乡的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回家的路。”
.“好,我一定办好”赵长贵
任璇儿到了卓码和阿美的面前,他刚想对卓码说几句什么,卓码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任大哥,不要走,好不好?”藏族姑娘没有汉人那么多拘束的礼节,爱就爱,喜欢就喜欢,不遮遮掩掩。直接一把抱住了他,任璇儿算是心肠很硬的人了,可他怎么不敢看卓码的眼睛,他怕看了以后,他心中会更难受,他想伸出手去推开她,可怎么也狠不下这个心来,他安慰卓码:“别哭了,大哥以后会去看你的。”
他忽然觉得两片又湿又软的嘴唇在了自己嘴上,他的心‘砰‘砰’地跳动起来,他伸出手紧紧搂住这个美丽多情的藏族姑娘,两人深情地吻着,刹那间,任璇儿忘记了自已是什么人、忘记了自己的仇恨、忘记了自已的抱负,他真希望时间就此停顿,好久,好久……
任璇儿大步朝前走去,他听见卓码在他身后叫道:“任大哥,我等你!”
任璇儿单人孤骑走在沙漠里,天地间一片空旷,他想起了那位博学多才的父亲教他的那首歌谣:
因为这份倔强,我背走行囊,
因为那个传说,我四处流浪。
岁月在我脸上写满沧桑。
等待让生命空旷凄凉。
对于得到,对于失去,
我没有去想。
我流着泪水把爱情埋藏。
我不是为了衣锦还乡,
也不是为了寻找梦中的天堂,
我寻找的是穷山涩水祖祖辈辈的—希望!
本文为「刀神传说」第二章:纵横大漠,返回全篇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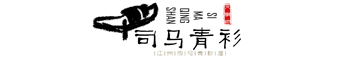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