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冬至,阴历冬月十六。早晨的水饺吃到了十点半。收拾完出门,去金山公园遛弯。日月如梭,前年的今日月夜登金山的情景如在眼前,还有文字如下:“2016农历11月16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携好友两个,欣然登金山。天冷无人,一切静默。皓月当空,月色,如水般空明澄澈,如纱般虚无缥缈。凉气袭人,却可以清醒红酒的微醺。我们随性侃山,朗声大笑,说笑声在空旷的夜色里飘荡,隐没……心情愉悦至极,沉醉其间,仿佛整个空间只属于我们。月光下的金山公园原来这么的静,这么美。”
今天好友没来,也不是夜晚。天气阴冷,公园里游人稀少,很是清静。女贞子的浓叶墨绿着,松柏生机勃勃,竹子苍翠丛生,楠木灌丛的红叶不逊于春天的新发,山体避风处的月季还有待开的花苞,台阶旁边的银翘居然有成串的骨朵和零星的黄花盛开。站立山顶看环山的柏油路,汉白玉的台阶,四角翘起如鸟翼的凉亭,绿树红叶,一切静美,美得宛如早春,少了寒冬的萧杀。
三四十年以前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冬天。万木凋零,天寒地冻,一切苍灰。
最冷的还是早晨。房顶上落一层厚厚霜,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就连厨房水缸里都是一层一层的冰碴子。上早学时从锅底下扒出头天晚上埋火灰里的红芋,有时候还一半生一半糊的(不熟的啃着也挺好吃,甜),用袄袖子夹着,走着,吃着,争着,抢着,抹得满手脸的黑灰,洒下一路的欢笑。课间取暖最好的游戏是挤加油,教室墙角被磨蹭地溜光,人人都是上下一身土,上课铃敲响,才一阵猛拍猛跺,教室里弥漫着朴朴的烟尘,许久才落定。
村里的水塘、沟渠封了凌,来回上下学的谁还走土路,一律下坑塘溜冰回家。有时也拿一个板凳,翻放冰上,大家轮流坐在上面,其他人或推,或拉,在冰上飞跑,翻滚。一坑塘的快乐,一坑塘的笑声。朗朗的笑声飘荡在冰冷的空中,伴着呼出的团团白气,还有冻得通红的鼻尖。
大水塘的冰冻得不太厚实,有不夜归的鹅鸭,在坑塘中央的一小片水里不停地游动。胆子大的男孩,喊着号子,在冰上用力齐跺,冰就上下颤颤地炸裂,裂纹弯曲如游蛇。听着咯咯渣渣的响声,心也惊得如裂了纹一般。当然掉冰窟窿里,湿了棉鞋,湿了棉裤的人常有。伴着同伴的嬉笑,少不了大人的打骂。推推搡搡地回到家,脱光湿棉衣钻到冰凉的被窝里,缩成一团。大人则用厚厚的沙土盖在湿衣服上猛踩一气,吸掉些水分,提起抖抖,放火盆旁烘烤。棉鞋棉裤烤糊那是常有的事。
最好的是下雪。那时候的雪下得干脆利落,下得勤,下得大。干雪堆在屋后、树下,一冬天都化不完。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谁的脖子里没有过雪蛋子的飕飕凉。上课进教室前还不忘抟一个雪球,在手里抟得流水。手指冻得如胡萝卜,还乎乎冒热气。等红日升起,房顶的雪化成水流下来,一边流一边结冰,长长的椎形冰凌挂满房檐,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煞是好看。用长棍打下几根,拿在手里,宝剑一般。当然也会时不时放嘴里吸一下,过过吃冰糕的瘾。整个冬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是大棉鞋,厚棉袄,厚棉裤,如笨笨熊样儿。
有太阳也好,暖暖的太阳照着小村庄。可以搬出上了冻的白菜、萝卜晒在院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双手抄进袖筒里,南墙根晒着太阳,抽着旱烟袋,蹲着,坐着,闲聊。到了饭点,大家端出一碗地瓜糊头,扛个大卷子,就着腌腊菜,臭豆食,白菜炖粉条,吃得入入贴贴。那时候的生活简单,幸福,快乐!
现在的冬天下点小雪、结点薄冰就稀罕得不得了。
今日的阴冷,也许在酝酿一场洁白的小雪吧。
文丨李艳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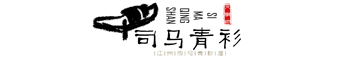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