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那“哗哗”的雨声传入高万祥的耳鼓,接着他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片亮光;高老爷子慢慢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灯如豆,一缕由艾蒿燃烧时发出的淡淡清香袭来,北方人夏季都用它来熏蚊子,这清香让高万祥感到了一丝家的温馨。
守在一旁的小翠儿姑娘忙凑上来,惊喜地说:“呦!老爷子,您醒啦?太好了!”说着话,小翠儿姑娘欣喜地一拍手,随后转身跑了出去,大声呼喊道:“郝大夫,那老爷子醒过来啦——”
闻讯赶来的郝大夫跟着小翠儿姑娘来到耳房中,他微笑着冲高万祥点了点头,笑着说道:“老爷子您……醒啦?”随后便坐在炕边,给高万祥号了号脉,接着说道:“脉像挺平稳的,这回没事儿了;您真命大呀!要不是那几个过路的把您及时送来,您受了枪伤,流了那么多血;再让大雨这么一浇,那可就悬啦……”
老人用舌头舔了下干巴巴的嘴唇,无力地问道:“我…我这是在哪儿?”
郝大夫笑着说:“在我家里呀!”
高万祥打量着眼前的郝大夫,疑惑地说:“您是……”
郝大夫笑了笑,接着说道:“啊,在下郝玉川;在沿河镇世代行医……”
高万祥不禁热泪盈眶,伸手抓住郝大夫,惊喜地问道:“先生难道就是沿河镇上大名鼎鼎的‘寿仙堂’的郝玉川郝大夫?”
郝大夫说:“正是!”
老人咧开嘴苦笑了一声,激动地说:“落难之人在这儿能遇到您,也算我的造化了。”
郝大夫说:“请问老先生,您是……”
高万祥望着郝大夫,激动地说:“在下山西洪洞人氏,名叫高万祥……”
郝大夫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忙站起身来,重新打量了老人一番,双手一抱拳,激动地说:“老先生莫不是山西‘大通镖局’的老掌门,江湖上人称‘通臂王’的高万祥老侠?”
高万祥连连摆手,惭愧地说:“郝大夫您千万别这么说,啥‘通臂王’?那不过是大伙儿乱叫……”
郝大夫激动地说:“早就听武林的朋友们说:天下通臂数洪洞。老爷子,北京城里牛街那边也有一伙练‘通臂’的,南边儿涿州也有练‘通臂’的;我跟他们都很熟,常听他们提起您,江湖上谁不知道您‘通背王’的大名啊!”
高万祥叹了口气,羞愧地说:“郝大夫,败军之将,焉敢言勇?您瞧,这不是如今就活脱脱地‘现’在您眼前了吗?丢人哪——”
郝大夫连连摆手,板起脸来认真地说道:“前辈,您千万别这么说。那土匪在暗处,您在明处;他们手里又有枪,俗话说的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
老人摇了摇头,低声说:“江湖上讲究‘胜者王侯败者贼’,此次失了镖,‘高万祥’这个人就算……死啦。郝大夫哇,您应该知道:自古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呀!武林中人,失手就是个‘死’啊……”
郝大夫脸色阴沉了,叹了口气,冲高老爷子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武林中失手的人,简直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了呀!镖师一旦失了镖,就只有从此退出武林,隐姓埋名地“偷生”罢了。倒了自己的“招牌”,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往后再没人来请你去押镖,就等于断送了你的活路;你这个人就算完啦!
老人抓住郝大夫的手,焦急地说:“郝大夫,武林中人最讲信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此次被劫,丢了东家托付的‘镖银’,得赶紧写信告诉东家一声。郝大夫,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替我跑趟邮局,帮我把信发了呀!”
郝大夫轻轻拍了下老人的手,笑着说:“老前辈果然是个大丈夫,九死一生之际,还不忘别人的所托之事,佩服!请问您……此次统共被劫去……多少钱财?高老侠亲自出马,想来肯定不是个小数目吧?”
高万祥长叹了一声,低声说道:“我此次是受山西日升昌票号老掌柜的托付,押的是日升昌救命的钱哪!改号民国以来,票号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日升昌维持不下去了,这才关了北京的分号,把现钱变成黄金,运回总号。这笔钱要是丢了,日升昌老掌柜的不抹脖子也得上吊哇!”
郝大夫盯着高起祥的眼睛,问道:“前辈,您给日升昌写信,想说些什么呢?”
高万祥急切地说:“告诉东家,镖银被人劫了,那笔钱丢了,柜上别指望这笔钱救急了,让老掌柜另想办法。丢失的镖银我…日后一定想方设法还上。”
郝玉川冷笑了一声,说道:“晚辈冒昧地问一声,您在山西的家产……可够赔偿人家镖银的吗?”
高万祥低下了头,一时愣住了。他心里明白:就算倾家荡产,他也赔偿不了人家的“八千两黄金”哪!
郝玉川又接着说道:“自古道‘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倘若您的家产不够赔人家的镖银,您……又该怎么办呢?”
高万祥低声说道:“人不死债不烂……”
郝玉川冷笑了一声,冷冷地说道:“前辈,我可不怕您恼我;普天下谁不知道,你们‘山西老西儿’是有名的‘舍命不舍财’呀!我怕消息传到了山西日升昌票号,对您……不利呀!”
高万祥果断地说:“既然摊上这种事儿了,我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让人家抄家、没收财产,再把我送进大狱,我认了。”
郝玉川冲老人一伸大拇指,大声说:“您越是这样,郝某越是不能让您吃这个亏。武林中人讲究的是:人前一句话、马后一鞭子。可商人呢,他们讲究的是,将本求利,以小博大。讲究的是‘利’字当先哪。所谓‘无利不起早’,‘亲兄弟明算账’。说白了,那就是六亲不认哪!您丢了人家的钱,又赔不起人家;人家跟您的这‘仇’,那就算解不开啦!就算您愿意豁出性命来,要给人家一个交待;可人家领情吗?就算您豁出来打算为此去蹲大狱,可您的家人能不因此受牵连吗?倘若人家把您告到官府,前辈,您……要三思呀!”
高万祥脱口喊道:“翠萍,俺的宝贝女儿……”老爷子能不明白吗?被逼上绝境后,对方肯定能干出把他的宝贝女儿抓去抵债的事儿。随后就是抄家、封门……
高万祥登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起来。
郝玉川重新坐在老人身边,笑着安慰道:“前辈,您听我一句话,您现在什么都别想,踏踏实实地在我这儿养伤。您在沿河镇外遭劫,谅那些土匪总得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俗话说得好:‘贼不打三年自招’,早晚能抓到他们。咱们镇上的警察署长非常能干,郝某不才,绿林道儿上也有不少朋友;咱们想法子慢慢地寻访,一定能找到劫您镖银的那伙土匪,到时候让您手刃仇人,追回镖银,岂不快哉?依我说,破案之前……您最好还是别让日升昌票号的人知道为好。”
高起祥六神无主地说:“那…那得啥时候才能破得了案?万一破不了案咋办?不跟东家打声招呼,我高万祥岂不是成了无信、无义之人?”
郝玉川说道:“前辈,您刚才说,您家里……还有个女儿?”
提起女儿,高起祥眼里闪出亮光,动情地说道:“是,小女翠萍……今年十七岁,还没许人家……”
郝玉川正色道:“前辈,您听我一句话;就算为了您的女儿,也不能让日升昌知道您被劫的事儿。”
高起祥迟疑地说:“你是说……”
郝大夫冷笑了一声说道:“万一您被劫的事儿要是让日升昌的人知道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您的女儿……”话说了一半儿,郝大夫有意地打住了话头。
高万祥听出来郝大夫华丽的意思,脸上的肌肉不由得抽搐起来,脸上的五官挪了位,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郝大夫忙又劝开了……
一觉醒来,已是次日上午了。太阳透过镶在纸窗户下边的那块玻璃,照在高万祥的脸上。他挣扎着翻了翻身,环视了一下自己身处的这间屋子。从阳光照射的角度来看,这应当是间北房;顶棚上糊的纸已经发黄了,看来这是间老房子了。靠北边墙边,摆着一个大条案,上面的黑漆已经剥落了不少,看来这条案也是件老物件儿了。条案上方的墙上供着一张“药王”的画像,下边的铜香炉内点着香,旁边放着一些时鲜果品。条案前是一张老式八仙桌子,旁边放着两只雕花的太师椅,一看那木头,高万祥便知道那是“花梨木”的,一般寒门小户儿,用不起呀!八仙桌上放着一摞纸张发黄的线装书和文房四宝,桌子前边的地上摆着两盆儿高万祥根本叫不出名字的珍奇花木,给室内平添了几分雅趣。西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儿,从发黄的纸张来看,那也是有年头儿的东西了。可惜高万祥识字不多,根本认不全条幅上书写的内容。房子里靠东边,就是他躺着的土炕;北方的房子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看来,这房子像是郝大夫的书房。房间不大,但透着整洁、儒雅。
门帘儿一挑,一个姑娘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姑娘先侍候高万祥洗了脸,然后便端起那汤,一勺一勺地喂高万祥喝。才喝了两口,高万祥觉得这汤淡的没滋没味儿,便问道:“姑娘,这是什么汤啊?”
姑娘笑着说:“这是是郝大夫配的方子,我们太太亲自给您熬的汤。汤里有排骨、人参,别的就不知道了。太太说,您刚受了伤,得忌口,尤其得少吃盐;就只好让您受委屈了。”姑娘一口柔滑的“京腔”,让高老爷子听了很舒服。他甚至产生了幻觉:眼巴前儿的这姑娘,仿佛变成了他的女儿翠萍。高万祥用柔和的目光打量着小翠姑娘,又笑着问道:“姑娘,今年多大啦?”
“虚岁十七,属狗的。”
高万祥笑了,小声说:“啊……,这么说,跟我闺女一般大。那你是……”
“我是太太从娘家带来的丫头,叫‘小翠儿’。”
“你们……郝大夫呢?”
姑娘欲言又止,咳嗽了几声,才迟疑地说:“他上……上义地了。”
“义地?啥是义地?”
姑娘涨红了脸,紧张地说:“郝大夫……不让说,怕您着急。刚才警察署长马剑飞来,想要问您一些话,都让郝大夫给拦了。郝大夫说了,您受了伤,伤了元气,这阵子不让您多说话。”
“什么?你们郝大夫敢拦警察署长的驾?”
小翠儿把嘴一撇,不以为然地说:“马署长跟我们郝大夫是磕过头的把兄弟,他还得管我们郝大夫叫‘大哥’哩,怎么不敢拦他?”小翠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忙伸了下舌头,自嘲地说:“瞧我,又说走了嘴了;郝大夫说过,不让您多说话;我又唠叨起没完了。您歇着吧,我回去了;有事儿您言语一声,我马上就过来。”说罢,小翠儿收拾了碗,一挑门帘儿,像风似地飘走了……
见到小翠儿姑娘,高万祥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翠萍。由于媳妇去世早,女儿翠萍让他调教得像个“假小子”,打小就不沾针黹(指)女工,却喜欢成天舞枪弄棒。那年月,女人是要缠足的。可高万祥对女儿过分溺爱,不忍心让女儿受那份罪,结果翠萍姑娘竞成了“天足”。这样一来,姑娘的婆家可就不好找了。在一些男人看来,女人的脚越小越令他们有面子;那年头儿讲究的是“三寸金莲”嘛!翠萍姑娘尽管长得貌美如花,可受了一双大脚的拖累,在一些男人眼里,竟成了比“丑女”还要丑的女人,想找个称心的女婿可就费劲了。
心高气傲的高万祥却不以为然,不但不急着为女儿找婆家,反而放出话来:要为女儿招一个上门的养老女婿。
不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主儿,男人谁也不肯给人家去当“上门女婿”。而且,条件差点儿的小伙子,高万祥也看不上啊!翠萍姑娘的亲事高不成、低不就,一来二去,就把婚事儿给耽搁了。今天想起来,高万祥不免心中后悔。如果女儿早点儿有了人家,自己不是也少了一层牵挂吗?都怨自己考虑不周哇……
从女儿又想到了自己的家、武馆,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日升昌”的老掌柜。作为镖师来说,在“道儿上”混全凭一块招牌。倘若失了镖,那就算倒了牌子;日后再也别想干“这行”了。要想找回面子,那就得尽快把失了的镖再找回来。
退一万步说,丢了人家的货,就得如数赔给人家。高万祥越想越害怕,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头晕目眩,他赶忙闭上了眼睛。八千两黄金,他真的赔不起呀……
合上双眼后,七个徒弟的音容笑貌,便逐一在眼前闪过。这几个徒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把孩子交给他高万祥,实指望孩子能跟他学好武艺,日后好谋个给财主家去看家护院的“饭碗子”,靠“这个”养家糊口呀!然而,谁承望头一次到北京来走镖,就会惨遭不测,落一个“客死他乡”的下场呢?让他怎么跟人家父母交代?想到这儿,高万祥忍不住心痛欲碎,顿时老泪纵横……
不知什么时候,高万祥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醒过来时,已是中午时分了。小翠儿姑娘端来了一碗肉粥,把高万祥扶了起来,一口一口地喂开了。和早上那碗汤相比,这碗肉粥总算有些滋味儿了。高万祥其实早就饥肠辘辘了,但郝大夫却故意给他安排了“流食”,想来一定对养伤有好处吧。
转眼间,一大碗肉粥就吃光了。高万祥砸了咂嘴,笑着说:“哎呀,还……还差点儿,嘿……”
“郝大夫不让您多吃,说是您心里有火,得吃两天稀的。太太说了,晚上给您做片儿汤。”
高万祥央求道:“姑娘,能……能放两个鸡蛋吗?”
“不能!郝大夫说,鸡蛋是‘发物’,您的伤口没长好之前,不能吃。”说罢,小翠儿端着起空碗,起身走了。
小翠儿刚出门儿,郝大夫便领着一个身高体壮的警官,挑门帘儿走了进来。高万祥刚要起身,郝大夫抢先一步拦住了他,关切地笑着说:“老先生,您别动;躺着吧!”说罢,他坐在炕沿儿上抓过高万祥的手,号开了脉。之后,他长出了一口气,笑着说:“现在我敢说,您的脉象绝无凶险之兆,没大事儿了。”见高万祥一个劲儿的拿眼瞟旁边儿的那位警官,郝大夫忙笑着说:“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是咱们沿河镇警察署署长马剑飞,我的磕头弟兄。昨天您被人抬到我这儿后,马署长就带人勘验了现场,今天早上他就想找您问问情况,我怕您身子太虚,就给拦了。老先生,您现在就把您被劫受伤的过程跟马署长说说吧!”
马剑飞拎过一把太师椅,坐在郝大夫对面,打开随身带着的记录本,掏出钢笔,笑了笑,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问道:“老先生,恁……叫啥名字?”
“啊……,我叫高万祥。”
马剑飞又接着问道:“高老先生,恁还记得劫恁们的土匪是一伙啥样的人吗?”
高老爷子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会,又接着说道:“当时他们躲在小山丘上的酸枣棵子后边,只听见他们说话,没看见人。那阵儿天还没大亮,也看不大清楚。”
马剑飞追问道:“那……他们说话是啥口音?”
高万祥想了想,说道:“好像是……东北口音,有个家伙还骂了句‘妈拉个巴子’,对,他们是东北口音。”
马剑飞和郝玉川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点了点头,又问道:“老人家,恁被他们劫去了啥东西?听说恁们运的是一口棺材对吗?”
高万祥犹豫了,他不知道该不该跟眼前的这位警官说实话。按江湖规矩,一个镖师,特别是像他这样名冠三晋的镖师;是不应当借助官面儿上的势力来对付黑道儿上的强梁的。说到底,保镖的与劫道的土匪其实是一家人;而警察和早年间的捕头一样,属于“朝廷的鹰犬”哪!他要是跟警察说了实话,岂不成了江湖败类了吗?高万祥心乱如麻,不由得把脸扭向了一边……
马剑飞并未继续追问,他心里有数:像高万祥这么有名的武师,断不会从北京往山西押运一口空棺材。而劫匪下手之狠,肯定也不是为了劫下一口空棺材。高万祥越是不想说,马剑飞越是认定了被劫之物一定是一大笔巨财。他又随便问了几句,便把话题扯开了。他叹了口气,小声说:“高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何况,眼下天气炎热,您的七个徒弟又全是中弹身亡,尸体极容易腐烂。俺们警署已经一一作了尸检,之后来不及同您商量,就已经把他们都埋了。”
“什么?都埋……埋了?”高万祥急了,他没能亲眼看着自己的徒弟入殓,心里甚觉不安。
郝玉川忙笑着劝道:“高先生,恁放心;恁的七个徒弟入殓前都换了新衣服,警署还专门请人给他们化了妆,他们看上去毫无凶相。棺材都是五寸板的柳木做的,在沿河镇,这也算说得过去了。”
高万祥抹去脸上的泪珠儿,小声问道:“他们几个埋……埋在啥地方了?”
郝大夫忙说道:“都埋在沿河镇‘义地’了。沿河镇义地是郝某祖上置办的一块地,那儿埋了不少客死沿河镇的外乡人,也有铁路工厂里死去的的工人。”
高万祥不由得泪流满面,梗噎着说:“郝大夫,让我下辈子变牛变马来报……报答您吧……”说罢,老侠高万祥不由得哭出声来;马、郝二人又是一通劝慰。
见问不出什么名堂,马署长便起身告辞了。
郝玉川送走了马剑飞,继续陪高万祥聊天。他看出高万祥对马署长有戒心,便有意地说:“马署长这个人可是好人,他早先一直跟着冯玉祥将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受了伤,是我把他救活的,所以我俩后来就成了朋友。他养好了伤之后,就离开了队伍,转到了警界。别看他当了警察署长,可从不欺负老百姓。他自己不赌、不嫖、不抽大烟。办案认真、待人公正,在沿河镇也算是难得的好官儿了。“
高万祥此刻依然心乱如麻,对郝大夫的话,也没做什么反应。郝大夫见状,便告辞走了出来。
黄昏时,来送饭的人竟然换成了郝玉川的夫人荷香。
荷香夫人看上去大约有三十多岁,长得银盆大脸,体态丰盈,脸上虽带着微笑,却不失几分庄重,看上去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郝玉川得知了高万祥的身份之后,赶忙换成了自己的夫人亲自来伺候高老爷子。他早就听说过山西大侠“通臂王高万祥”的名号,可以说对高万祥仰慕已久了。此次高万祥落难正好落在了他得手上,他怎敢怠慢?让自己的夫人来伺候高老侠,正表达了他对高老侠的一片仰慕之情。
高万祥得知了荷香夫人的身份后,顿感到诚惶诚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荷香夫人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显得十分亲热、自然。高万祥知道,这是人家郝大夫把他当成“自己人”,才让自己的夫人亲自来服侍他的。高万祥感到非常不安,说话都结巴了。双方在交谈中,高万祥得知郝大夫今年三十有七,却还没有儿女。这让他颇为郝大夫不平:像郝大夫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没有后代呢?老天真是不公!
之后,每顿饭都是由荷香夫人亲自送来,亲自喂高万祥吃。她还耐心地侍候高万祥洗、漱,陪高万祥聊天。而郝大夫却一连十几天没再露面儿,高万祥询问起来,荷香夫人便说,丈夫带着伙计上安国县进药材去了。
高万祥的腿伤一天天的渐好,但心情却越来越烦躁。他根本不相信郝大夫会去了安国县,郝大夫躲着他,一定有人家的道理。然而,他的心像长了草一样,乱哄哄的。他能不急吗?万一他失了镖的消息传到了山西,人家要是一怒之下,把他的宝贝女儿扣下可怎么办?若是郝大夫在跟前,他还可以跟郝大夫商量一下,让郝大夫帮他拿个主意。可天天陪伴他的只有荷香夫人和几个伙计,这话让他怎么说得出口呢?
这天饭后,俩高老爷子又和荷香夫人在一起闲聊;荷香夫人竟然说:“大哥呀,您找机会劝劝我们‘当家的’;他都奔四十的人了,我又一直没有为他生儿育女,怪对不住他的。可再怎么说也不能让郝家绝了后哇?我劝了他多少次了,让他纳个妾、讨个小;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大哥,他敬重您,您面子大;您替我劝劝他呗!”
“啊……行。”高万祥胡乱地应承着,他没有理由不答应啊!
荷香夫人小声儿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郝家的‘正骨膏秘方’,是传男不传女的。您说我们‘当家的’要是没个儿子,这‘正骨膏’往后岂不是就要失传了吗?再者说,像他这样的身份,家里娶个三妻四妾的也平常啊!”
高万祥突发奇想:要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郝大夫作妾,不是一举几得的好事儿吗?头一宗,自己受了人家的救命之恩,把女儿嫁给郝大夫,也算是一种报答了。其二,郝大夫是好人,荷香夫人看来更是贤惠;女儿若是嫁到郝家来,虽说是做“小”,但肯定也受不了委屈。把女儿安顿好了,自己日后行走江湖,寻找仇家去报仇雪恨,不是也无牵无挂了吗?想到这儿,高万祥脸一红,嘿嘿一笑,试探地说道:“弟妹呀,我看小翠儿这姑娘……就挺不错,你让郝大夫把她收了房,不是挺好吗?”
荷香夫人叹了口气,小声说:“小翠儿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丫头,本来收她做妾……也没什么不可以;怪只怪当初我嫁过来时,我们当家的见小翠儿聪明好学,就常教她看医书、背汤头儿歌。后来,经人一撺掇,他就认小翠儿做‘干女儿’了。这么一来,‘收房’的话也就不能再提了。”
高万祥见机会来了,忙鼓起勇气说:“弟妹,我有个想法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荷香夫人微笑着说:“呦,大哥呀;您……还客气什么?想说就说呗!”
“好!”高万祥心里直扑腾,他清了清嗓子,结结巴巴地说:“弟妹,那我……我可说啦!”
“我这儿听着哩!”
“弟妹呀,人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郝大夫救了我一命,我……我实在是无以为报哇!要是……要是郝大夫……不嫌弃,我情愿把家中的小女翠萍,嫁给他做妾;还望荷香夫人能成全此事……”
话一出口,高万祥头上就冒出了汗。真够难为他的,从古到今,哪有当爹的主动向人家提出:把自己的女儿许人作妾的呢?此话一出口,高万祥不敢再看荷香夫人,忙把头扭向了一边。
荷香夫人先是一惊,随后紧跟着追问道:“老人家,这话可是您说的,您……可不许反悔!”
“高……高某一片真心!”
荷香夫人眼珠儿一转,满脸堆笑地说:“那您等着,我这就去找我们当家的;咱们干脆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这事儿定下来。我这就去找他!”说罢,荷香夫人站起身来就朝外走。
高万祥忙说道:“你不是说他上安国县进药去了吗?”
荷香夫人转回身笑着说:“那是我蒙您哪!当家的怕您不能安心养伤,光惦记报仇的事儿。他躲开您几天,您总不会跟我一个妇道人家谈报仇的事吧?他现在就在前院儿柜上,我这就去叫他。老爷子,您可不许反悔呀!哈……”撂下一串笑声,荷香夫人兴冲冲地离开了高万祥住的偏房,快步赶奔前院,向丈夫去讲述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
早年间,女人过门后没有为丈夫生儿育女,那可就算犯了“七出之过”。所谓“七出”,就是男人七个可以公开休妻的理由。具体就是指:一出:不孝顺父母。二出:无子。三出:淫荡。四出:忌妒。五出:多言。六出:有恶疾。七出,盗窃。就凭这老规矩,丈夫倘若一纸休书“休”了她,也无可非议。对此,荷香夫人因为一直未育,既感到愧疚,又由衷地感激丈夫的大度、宽容。她早就打定了主意:倘若丈夫真的因为她的“无出”休了她,她就投永定河自尽;绝不会回到娘家去给父母脸上抹黑。多年来,她一直胆战心惊地在这个家中小心翼翼地和家人相处着。一旦有了帮丈夫“讨小”的机会,荷香夫人的态度自然是十分积极的。这次人家高万祥老爷子主动提出来: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郝大夫作妾。这可是打着灯笼也没地方去找的好事儿呀!人家高万祥也算武林豪杰,江湖大英雄;若能娶高家女儿作妾,也算不辱没了郝家。荷香夫人打定主意:这次她一定要说服丈夫,尽快促成这段姻缘。
然而,一想到要和别的女人一起来分享自己男人的爱,荷香夫人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儿。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泪水竟然成串儿地淌了出来,怎么也止不住。
郝家的这套宅子,是北京地区典型的“四合院”的格局。沿河镇大街是南北走向,街里居民的宅院分列大街两侧,都是“东西走向”的。所以,沿河镇临街的院落,没有坐北朝南的“宅院”,不是“朝东”就是“朝西”。田宅坐西朝东,自地面至大门口儿,共是五级青石板铺成的台阶。台阶两侧各有一个一人来高的石狮子,看上去格外气派。狮子两旁各栽着一棵粗壮的槐树,看来那粗壮高大的槐树也有年头儿了。盛夏时节,两棵槐树的树冠把寿仙堂药铺门前的上方遮的严严实实,门前的空地上绿荫生凉,别有一番情趣。那年月,玻璃在民间还很少见,但田宅临街的这一面的门窗却都装上了玻璃,药铺里的一切从大街上便可一览无余,店铺内也显得格外亮堂。台阶以下的根基不算,仅从店铺的地面到屋顶,就高达一丈二。像这么高的民房,沿河镇仅此一家。更让人称道的是,田宅所有建房的柱、梁、柁、檩,都用得是清一色的“金丝楠木”。据说这种木料是从南方运来的,除了结实,这种木材还具备“水不浸、蚊不穴,不腐不蛀不生虫儿”的特点。当然,那价钱也就可想而知了。能用得起这么昂贵木料建房子的,可着宛平县内,再也找不出第二家来。郝家的富有,由此可见一斑。
和其它的民居、店铺不同的是,寿仙堂的大门却并不气派,甚至形同虚设。夏天,门口儿挂着由珠子穿成的“珠帘”,冬季则挂上一条棉门帘。这是因为郝家行医,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人上门求医、请大夫出诊、抓药。所以,寿仙堂的大门是永远不关的。
进得门来,宽敞的店铺内排满了装着各种药材的药柜子。柜台前总也断不了前来抓药的人,里边的几个伙计熟练地为客人照方抓药,边抓药还要边念叨着。有些药需要捣碎,伙计们便把称好的药放在柜台上铜制的“药臼”内,然后用“药杵子”一通有节奏的捣动,最后便把捣好的药末儿倒出来,或单包、或和其它的药包在一起,再仔细叮嘱客人一番,才把药递给客人。三四个伙计忙而不乱,看上去很有章法。
大厅北侧,用八幅雕花的屏风隔出来一块地方,靠临街的窗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号脉用的“药枕”和笔、墨、纸、砚,这里便是郝大夫为病人诊脉的地方。
不远处放着两条长板凳,候诊的人便坐在长凳上,依次排队等候着。靠北边的墙根,还支着一张床,那是专为需要按摩、推拿、复位的病人准备的。外行人不了解,以为当大夫挺轻松的。其实,骨伤科的大夫给病人推拿按摩,可绝对是个力气活。尤其是给脱了臼的病人复位,通常郝大夫都得叫别的伙计来帮忙,碰上那些腰部脱了臼的伤号,他还得把病人的身子背靠背地背起来,然后使劲背着病人原地往起跳,才能帮着病人脱了臼的关节复位。在病人杀猪般的嚎叫声中,郝大夫和伙计都累得通身是汗,才能完成治疗的过程。那场面胆儿小的真不敢看。时间长了,药铺里的伙计、账房先生、郝大夫的使女小翠儿,做饭的冯嫂,也都学会了简单的推拿按摩。特别是一些女病人,那就非得让荷香夫人、小翠儿和冯嫂为她们帮着治疗了。
郝大夫的高超医术是祖传的。他家祖上曾经是跟随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了北京的军医,跟随李自成的义军从河南打进了北京城。进了北京城后,郝家先祖对李自成的农民军的所作所为很失望,就脱离了义军队伍,在北京开了诊所行医。后来李自成的军队退出了北京城,郝家老祖并没有跟随李自成的军队一起撤离北京,他躲了起来,甚至更名改姓,老老实实地在北京城当了治病救人的大夫。凭着精湛的医术,郝家在京城立住了脚,逐渐地还有了声望。清乾隆年间,郝家的当家人还曾入了太医院,当了御医。但时间不长,郝家的当家人就辞去了太医院的美差,卖掉了在北京城里置办起的宅院,举家搬到了卢沟桥西边儿的沿河镇落了户,继续行医。传到郝大夫这一辈,郝家人的医术更加精湛了;各科杂症都能治,只不过在骨伤科上最为拿手就是了。郝大夫向病人收的诊费也很奇特,一般的铁路工人、农民、贫穷的市民,他只收十个铜板的诊费。对那些家里遭到了横祸的穷人,他不但不收诊费,甚至连药费也免了。他这辈子不知救治了多少素不相识的外乡人,但对人家送来的牌匾,他却一律拒收。他常说:“大夫的医术高低,得由老百姓说了算;人家送你一块牌匾,恭维你‘妙手回春’;哪天你凑巧治死了一个,怎么向人家交代?是不是也会接受病患家属送你一块‘庸医误人’的大匾挂在大厅里呢?还有什么‘华佗再世’,那更是笑话了……”
同样是这个郝大夫,对那些有钱的主儿、名声不好的人;他一开口便要收他们三块现大洋的诊费,甚至还会更高。为了让那些出了大价钱的主儿心里平衡,郝大夫就常对他们说,自己是按照病人“命”的贵贱来收费的。那些“贵人”该付出的医药费,当然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贵”啦!
经他这么一说,那些花了大价钱的主儿,也只好无奈地苦笑了。在那个年月,三块大洋能买三袋儿面粉哪!自然,有钱人的药价儿也跟穷人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方圆几十里的范围之内,说郝大夫坏话的人也有。
寿仙堂药铺永远那么红火,每天到寿仙堂求医的人,把个不算小的大厅,弄得人头攒动,满满当当的。
大厅后边,便是田宅的前院。北房五间,南房五间,还有四间西房,另一间本该盖房的地方,成了前院通往后院的“过道”。前院住着的是账房先生和药铺的伙计、徒弟,另有一间灶房。宽敞的当院地上铺着大号儿的青砖,几棵粗壮的槐树长的遮天蔽日,让前院的房屋很难见到太阳。
穿过前院儿的“过道”,便是田宅的后院。五间北房,住着郝大夫夫妇和使女翠萍,厨师冯嫂。侧面的四间西房,是郝大夫家用来招待客人的。另一间的地方,便是厕所。正房对面儿最靠墙根儿的五间东房,却是长年锁着的。那是郝大夫配药的场所和库房,除了郝大夫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准入内;连荷香夫人也不行!原本,后院的庭院中也种了几棵槐树;后来郝大夫嫌它的树冠太密,遮住了阳光,就叫人把树砍了,改种了很难长得太高的丁香。如今,这几棵丁香树也长到一人多高了,每逢春天,那浓烈的香味儿能飘出老远,田宅的前后院儿都是香的。
俗话说,吃饭、穿衣亮家当。郝家的这套宅子,不知引起了多少人犯了“红眼病”。几乎所有在沿河镇露过面儿的“风水先生”,都异口同声地夸奖田宅“有风水”。不说别的,单说那种“金丝楠木”,如今你就是舍得花钱,也没地方去买呀!也就仗着郝大夫在黑、白两道儿都有朋友,搁一般的主儿,肯定早就被别人算计了。几乎沿河镇所有的财主都在暗自谋划着:“有朝一日,自家也要盖一所像寿仙堂那样的宅子……”
荷香夫人来到前边柜上,伙计们都主动地和她打着招呼。病人中也有和荷香夫人熟悉的,自然免不了一通寒暄。荷香夫人走到丈夫身边,俯在丈夫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郝大夫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小声说:“我把这几位侍候完了就回去。”
给跟前儿的病人看完病,郝大夫赶紧抓空儿回到了后院儿,来见高万祥。他挑开门帘儿,双手一抱拳,笑着说:“怠慢了,老前辈见谅啊!哈……”
高万祥忙起身相迎,郝大夫快步上前按住了他,然后轻轻打开高万祥大腿上包着的纱布,看了看伤口的愈合情况。他长出了一口气,又给高万祥包好伤口,微笑着说:“伤口长住了,明天就可以用我的‘正骨膏’了。不出一个月,我保证您能下地自己走路。”
高万祥苦笑了一声,叹了口气,小声说:“郝大夫,您不用安慰我;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啦!”高万祥从小随父练武,在武行中摔打了大半辈子,受伤何止十次、百次?民间有句俗话,说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像他这样大腿骨裂的伤,至少也得在炕上躺上一百天,怎么可能像郝大夫所说的“一个月就能下地自己走路呢”?
郝大夫看出高万祥对他的话并不信服,也没解释。他坐在炕沿儿上,拉住高万祥的一只手,说道:“老前辈,听内人说,您有话要对我说是吗?这不,我赶紧就过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郝大夫认定:高老爷子急着找他,准时还要急着给山西的东家,也就是“日升昌票号”的掌门人;写信告知对方所托的镖银被劫的事。郝大夫心里有些犹豫了,老人若是再次提出“那话”,他该怎么应对呢?
高万祥偷眼看了看郝玉川,从郝玉川脸上的表情来看,荷香夫人并没有把他的意思明明白白地告诉郝大夫。这可真让高万祥为了难,该怎么开口呢?俗话说,一家女,百家求。男婚女嫁的事,哪有女方主动开口的?何况是给人做妾,他高万祥的闺女,不应该这么“不值钱”呀!他长叹了一声,脸上呈现出了为难的神色。
郝玉川微微一笑,说道:“前辈,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您何必争这几天的工夫呢?马署长已率员四处查访了,我也托了绿林朋友,探访那伙土匪的行踪。谅那伙土匪也逃不掉,给您报仇雪恨,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罢了。”
高万祥苦笑着摇了摇头,小声说:“我如今躺在这儿,连动都不能动,哪儿还敢想报仇的事儿?郝大夫,这你可猜错了……”
郝玉川满腹狐疑地眨着眼睛,不解地问道:“那您这是……”
高万祥抬眼看了看郝大夫,愣了片刻,才用低沉的语调说:“郝大夫,干我们这行的,脸面要比性命值钱哇!何况我高万祥在江湖上又有个虚名儿,此次栽了跟头,可正应了一句俗话——抬得高、摔得响;露多大的脸、现多大的眼哪。从今往后,别说‘武行’这碗饭吃不成了;就是偌大的山西省,怕也没有我高万祥的立锥之地了。咱……咱丢不起那个人哪……”
“前辈言重了。人常说,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千里马也难免失蹄;你们山西的关老爷英雄了一辈子,不是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吗?”
高万祥连连摆手,用凄凉的语调说:“郝大夫啊,你……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这一行啊!干武行的,讲究的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行跟别的行不一样,比方说,做买卖的赔了钱,还可以接着再干。你们当大夫遇着有人得了那该死的病,也只能干瞪眼。但并不会因为您没治好哪一个病人,就不准你继续行医了。可我们这行却不同,我此次失了镖,若不能尽快手刃仇人、追回丢失的货物;今后便只有把脑袋掖进裤裆中,隐姓埋名,彻底退出江湖了。实不相瞒,我此次押的镖,那可是山西‘日升昌票号’的八千两黄金哪!老掌柜虽没有跟我明说,但是我明白:人家是急等这笔钱救急呀!这钱丢了,老掌柜不抹脖子也得上了吊啊……”高万祥说不下去了,不禁紧锁双眉,闭上了眼睛。
郝大夫看着老爷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高万祥接着痛苦地说:“郝大夫,我高万祥要够条汉子,我就应当回到山西,跪在人家跟前,任凭人家处置。自古道‘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人家就是把我一刀杀了,也不过分。八千两黄金哪……”高万祥狠狠捶了下炕席,长叹了一声,又小声说:“话又说回来了,人常说:争气不养家,养家不争气。一想起我的宝贝女儿,我……我又下不了那个狠心。您想想,人家就是把我杀了,不是也找不回那八千两黄金吗?人常说:父债女还。人家损失惨重,情急之下,肯定要在我女儿身上出气呀!孩子没招谁、没惹谁呀!郝……郝大夫,你……好人做到底,求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女儿吧!”说到伤心之处,老侠高万祥不由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郝玉川忙劝道:“嗨,这算不了什么。老前辈,您赶紧写一封信,我派人去太原把令千金接来,不就万无一失了吗?不是跟您吹,直、奉两系军界,我都有不少朋友。你们山西阎长官派在北京的办事处里,我也有至交。求他们派辆军车,再派上几十个弟兄武装护送,回山西去接您的女儿,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高万祥眼睛一亮,止住了哭泣,急切地问道:“此话当真?”
“高老前辈,您看我郝某是那号吹牛的人吗?咱豁出去破费点儿银子,这事儿好办。您得亲笔给高小姐写封信,要不然,高小姐能贸然跟一伙‘丘八’上路吗?别说日升昌的人不知道,就算他们知道了,哪个大胆敢拦军车?”
高万祥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连声说:“不妥、不妥,俗话说得好,‘当兵二三年,见了母猪赛貂蝉’。那些‘大兵’平日里还经常糟蹋妇女,让我女儿跟他们一块儿来北京?一千多里地呢!万一路上出点儿什么事儿,我……我岂不是害了我女儿吗?”
郝玉川沉吟了一会儿,突然猛地一拍大腿,说道:“我亲自去接!拉着他们的长官跟我一起去;看他们哪个混蛋敢当着他们长官的面儿对高小姐不敬?这……您总该放心了吧?”
高万祥还是一个劲地摇头,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郝大夫,我相信你是个正人君子,可别人……会怎么说?你跟我女儿素昧平生,你去接她,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舌头底下压死人哪!郝大夫,您……还是再琢磨琢磨吧!”
老爷子心里这个急呀,心说:这位郝大夫他怎么这么不开窍儿呢?
郝大夫脸一下子红了,他干笑了两声,为难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可是,我……我实在是没主意了。前辈,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话说到这儿,高万祥不禁脸红了。要让他面对面地跟郝大夫把“那话”说出来,真够难为他的。可到了这个份儿上,不说不成啊!高万祥闭上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最后睁开了眼,鼓起勇气,对郝大夫问道:“郝大夫,我听说……您现在还没有儿、女,是真的吗?”
“啊,这个……;是。”郝大夫觉得十分尴尬,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谁敢当着面儿把“这话”说出来。老话儿说得好: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嘛!高老爷子不是那种说话不知深浅的人哪!他怎么……
高老爷子却根本就不看郝大夫的表情,接着又说道:“老辈子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郝大夫就没打算……娶妾续小吗?”话一出口,高老爷子觉得自己的心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他不敢直视郝大夫的目光,忙扭过了脸去。
郝玉川更糊涂了,真搞不懂:高老爷子干嘛要跟他说“这个”呢?他纳不纳妾跟他去山西接高小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嘿嘿一笑,红着脸小声儿说道:“朋友也劝过我,‘贱内’也多次跟我提及此事;可……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怕得是贱内……伤心哪。老话儿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的夫妻似海深’。贱内为人十分的贤惠,我怎么能……。再者说,就算我打算纳妾,也没有合适的呀。大宅门儿里的妻、妾之争我看得多了,弄不好那就是一堆麻烦哪!”
高万祥心里这个起急,他搞不懂:这郝大夫是存心要他的“好看”吗?还是“傻”得不透气儿?他不能再这么打哑谜了,干脆厚着脸皮把话挑明。高万祥微微一笑,仗着胆子抬起头,望着郝大夫,真诚地说:“郝大夫,我有心把小女许你为妾,不知……”
郝玉川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涨红了脸、连声说:“不,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郝大夫真的慌了,他可从来没想过“这事儿”呀!人家现如今落了难,他要是趁机娶了人家闺女做妾;那不是“趁人之危”吗?他要是这么干,往后还让他怎么见人?不能啊……
“郝大夫,人常说,救人一命……”
“前辈,您这是骂我!行侠仗义,乃英雄本色;救死扶伤,是医者的天职。我若趁机娶令千金做妾,我的一片好心岂不付之东流?江湖上的朋友该怎么看我?非骂我趁人之危不可呀!别的事都好商量,这事儿……万万使不得呀!”郝大夫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他打定了主意: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
高万祥见郝大夫力辞,心里反到更加敬重郝玉川的人品了。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郝大夫,你所说的是常理。可眼下是啥情况?你若不依我,就是害了小女呀!难道你愿意让人家把我女儿卖到……妓院里去?或者让我女儿毁在一伙‘大兵’手上?你想过没有,小女跟你从山西来到北京,日后别人会怎么说?我女儿担此虚名,日后还怎么再谈婚论嫁?
“哎呀!高老前辈,这话我可担不起呀!我……我觉得,让令爱为我做妾,实在是太……太委屈她了。”
“郝大夫,眼下的情形是:你要不肯娶她,才真正是害了她呢。怎么?难道你非要让我给你跪下不成吗?”
郝大夫被逼得实在没话可说了,便支吾了一阵子,小声嘀咕道:“我怎么也得请出个媒人来提亲哪!还有什么‘合八字’、送彩礼……”
“一切从简吧!你可以把你和小女的生辰八字找人合一下,要是小女不是克夫的‘白虎星’,咱就把这事儿定下来,然后你去山西接她来北京,然后咱们马上就办事儿!”
至此,郝玉川再无话可说了,他要了高小姐的生辰八字,出门去了。
经算命先生一推算,俩人的生辰八字非常相合。于是,三天之后,郝玉川便坐上晋军驻京办事处的一辆军用吉普车,又带了一卡车护兵,浩浩荡荡开奔山西,接高小姐去了……
文丨梁亚明
下一章:风雨沿河镇第3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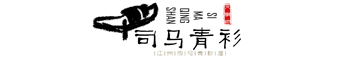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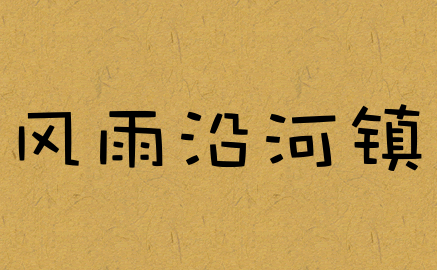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