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放寒假回来了,瘦棒棒。南方的白米饭咋就喂不肥他呢。去看大夫,大夫说挺健康,有点脾虚。反正他这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寒假也没别的事可做,那就中药调理调理。同事笑话我,孩子从小就不胖,早干啥来,当妈的后悔不,内疚不。想想也是,早先咋没给他调理调理呢?六包草药提在手里,有点紧张,我不会熬呀,朋友告诉我可以让药房代熬。又折回到医院询问情况。大夫说:自己回家熬就可以,用砂锅,铝锅,不锈钢锅,搪瓷盆都可以,先加三舀子凉水浸泡半小时,开锅后小火慢熬半小时,滤出就可以了,傍晚再涝一遍渣儿。我细心地记下,就差没录音备份了。
一直认为熬中药是一件很严肃很神圣的事:小小的火,专用的锅,还得专人守着,不时地用筷子试试水的多少。当然这都是看来的,我从没熬过,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好。如今,听大夫一说,感觉也不是多难的事,那就回家慢慢享受精心熬草药的幸福吧。
家里有铝锅不锈钢锅,甚至新的搪瓷盆也有,就不买砂锅了。涮好铝锅按大夫说的加水泡药,然后上煤气灶开始熬。儿子坐在旁边陪着。锅还没开,他网搜熬中药不能用铁锅或者铝锅。我赶紧停火换不锈钢的。娘俩紧张又好奇地守着,一会我用筷子搅搅,停会他又用筷子拌拌,还不时挑起一味药,研究这是陈皮,那是干柠檬,那个飘在水面的叫不出名的是无花果的浓缩版,沉在锅底的像黄豆瓣,可是熬到底都不膨胀,棒棒硬,一搅哗啦哗啦响……研究了半天,哪味草药的名字也叫不出。
沸腾着的汤水由茶色变金黄,变褐色,由透亮到浑浊,带着药香味儿的热气在锅口上升腾,散开,弥漫全屋,温暖,香甜,清苦,感觉还挺入鼻子的。开锅后小火熬了半小时,可是锅里的水还有很多,这咋能喝得下。老友桂梅交代我熬很一些,半碗药剂量就行,忒苦,难下咽。那就熬吧,我们交替着用筷子搅动草药,时刻盯着药汤水的多少。终于熬得差不多了,滤到碗里,一碗。我问儿子能否喝完,他说试试吧。喝了两口,咋吧咋吧嘴,说还行,不太苦,还非得叫我尝尝。三十多年没喝过汤药了,闻着药味,我还是有点心里怯,浅尝一下,苦得想吐舌头。可在儿子面前也不能露出难色呀。晚饭前熬的第二遍就淡了一些。儿子一气喝完,看他喝了两次,并没犯难,还很轻松,也许没有我记忆里的那么苦,那叫一个真苦。
十岁前的我身体弱,一到冬天就犯气管炎。吃药,打针,喝汤药等等都是家常便饭。西药丸是一把一把的咽,针是一天两次的连打十多天,回回都是左屁股打了右屁股打,针眼摞针眼,疙瘩连疙瘩。小胳膊是受不了那份疼的,那疼不是针头扎进肌肉一瞬间的疼,而是液体注入肌肉后长久的疼。那青霉素链霉素打下去疼得钻心,疼得持久,板凳不能坐,走路都困难。此外,还遍吃各种偏方,母亲不会放过听到的任何一个治气管炎的偏方。都说冬病夏治,夏天哥哥们从水坑里摸到老鳖,大大小小的都熬给我喝了,不加油盐的清煮,吃肉喝汤,还被警告:不能说腥,老鳖有灵性,愈说腥愈腥。喝完后的老鳖盖一个个挂在门框旁,晾晒干了,冬天擀碎烙老鳖骨头饼,一冬天都是被逼着吃干的腥气饼。想不清,为啥那时候坑里塘里的老鳖咋就那么多!还有用稻糠和泥包住草鱼,放锅底下烧熟了吃,草鱼肚里塞满了药引子,难吃的没法。过年时村里有杀猪的,母亲就去要来猪苦胆,趁热,叫我生生整个吞下。相比之下,那热的鸡苦胆,鱼苦胆,就要好咽多了,只差没逮条蛇剥了取胆吃。那些鲜姜炒鸡蛋,老醋煮黄鼠狼肉等还是挺好吃的。至今回味。
我是愈到年关咳喘得愈厉害。母亲一边忙年一边忙着带我去医院。冰凉的体温表夹在腋下,冰凉的听诊器在胸口滑动,老大夫冰凉的望闻问切简单又简单:还是老毛病,还是老药方,吃药打针不见轻,要不喝几幅汤药?大夫从满是小抽屉的中药柜子里,用精致的黄铜小杆称,一一盛出、称好各样药材,放在四方草纸上,草纸也是淡淡的药汤色。小心包好,纸绳子系上,捆在一起一大提。每次都是母亲背着我,我提着药包,药包在我们娘俩面前晃荡着,晃得我眼花,不一会就在母亲背上沉沉睡去。回到家,母亲放下我,在厨房灶堂前用三块砖支起那个把柄都磨亮了的黑砂锅(砂锅质地是真的黑,黑里泛青,外面是烟火熏的灰黑,粗糙,沉重),放药,加水,浸泡。然后点火熬治。火势不能大,柴要不断续,少了容易灭,多了火头太旺。温火慢熬,很是费时。熬好后,用包药的纸避住药渣,滤出药汤。一看见黄褐色的药汤顺着纸角流进碗里,我就哭着跑一边去。每次都是白开水碗,药碗,糖罐一字排好,母亲连哄带骗加嘿唬,强摁住,捏着鼻子硬灌,喝一半,洒一半。不知道是母亲的偏方管了用,还是医生的老药方有了功,过了十岁,气管炎奇迹般地好了,再没犯过,每年冬天吃药打针的艰难历程宣告结束。从那再没喝过中药,每到年关,院子里不再是草药味油烟味掺半了。可草药的气味深深地留存在记忆里。其实我不讨厌草药味。有时经过中药店,店里飘出浓浓的中草药味,我都会不自觉地深吸几下鼻子。
药汤是苦涩的,回忆是香甜的。草药的香味弥漫在房间里久久没散,有股很亲切的,很熟悉的味道,在这个特别的寒假!
文丨李艳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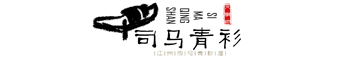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