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有件很重要的事:串门走亲戚。快乐、热闹也挺累人。一年一个时候的,那门子亲戚走不到就好像对不住似的,日后见面不好说话。好在,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交通便利了,一天走个五家六家的不算事。在亲戚家吃饭的事也大多免了,彼此都清静。(回娘家例外。)
以前,走亲戚可是一天只能走一家,必须是吃了饭再回的,时间都耗在了路上。家里年前所有年货的准备大多都是为了年后的待客。
记忆中我家待客的战线拉得挺长,一入腊月就陆陆续续有客人,年后过了元宵节还偶尔会有远亲来。我家是家族的长支,老客少眷,都要来我家吃饭,俩菜四个菜的要认真招待。最盼望任城的四姑家来走亲戚,因为能带来我爱吃各种鱼虾。也最喜欢跟着父亲去四姑家走亲戚,因为他们庄东就是京杭大运河,就是南阳湖,水波浩淼,鹅鸭成群,芦苇成荡,藕荷满塘,还可以摇摇晃晃地划船,撒网,有很多我们家里没有的稀奇好玩的水乡事。
最害怕嘉祥大姑家来走亲戚。虽然只有一个表哥一个表姐,按说客人不该多,可是老表家的近门子多呀,一听说去东乡里走亲戚,都要跟着来,反正年后闲着也没事。他们通常套辆村里的大马车,车尾放几个条篮子,装上几斤果子几斤糖,一提馓子,几块山上的芋头啥的,用自家织的蓝格子粗布手巾盖着。东西不多人挺多。老老少少满满一马车,路途遥远,丁丁当当一上午,到我们家恰好午饭点。每年来了都得坐上个两桌三桌的。我和哥哥是从来轮不到上桌吃饭的,蹲在厨房锅门口,馍馍就剩菜,筷子都用不上,更不用说板凳了。理由是客人们都坐不下,自家小孩就免了。母亲是忙得没空吃饭,人多乱得也没心思吃,还得时刻准备着上馍、舀碗、招待跟来的小孩子,发个三毛两毛的压岁钱。等客人吃完撤席还得收拾碗筷,端茶送水的。然后还要去收拾客人带来的礼物,见样留一半,回去一半,然后再给每个家什里装上俺家蒸的年馍:实团的馍几个,菜馍几个,玉米黄面豆沙的几个,白面枣馍几个,各自分清。亲老表远老表都说:妗子做的菜好吃,蒸的年馍更好吃。每年西乡的客人来后我们家几乎是被席卷一空,吃了喝了再带上。母亲总是说,西乡里山地薄,收成差,给他们带些年馍换换口味。年年如是。
年前蒸馍都得计划好蒸多少锅,多少样,吃多少,送人多少。过油菜也得变很多花样,每一样都是待客的一道菜。炸丸子,过藕棒,过藕夹(藕切半寸段中间割口夹上剁好的肉馅,挂面糊,下油锅),过假酥鱼(新蒸的馒头剥皮,搙碎,用酱油、材料面、葱姜末、鸡蛋清、盐、面粉等调好,用舀饭的勺子舀成小鱼形状,下油锅炸),过鸡块,过鱼块,过小草鱼等。后来母亲还做过滑丸子,滑肉啥的。我们只有吃丸子和藕棒的份,其余过油菜都被母亲用条篮子高高地挂在梁头的钩子上,只有客人来了才上桌。
还要煮大肉,劈材火烧得旺旺的,大块肉在锅里沸腾,撇掉血沫,加好材料,那就慢慢煮吧。其间母亲要不时用筷子插插,怕煮不烂,也怕煮得过烂。煮好后,捞到和面盆里,一部分留大块,有客人时切了烩菜。一部分切片再放回材料肉汤里煮一会儿,然后一起舀到盆里,可以吃肉冻,可以烩海带,来了客人挖一碗馏上就是是一道最硬的菜。
家里养的大公鸡也要在年前杀好的。热水没烫之前,父亲要把公鸡脖颈和尾部的翎羽拔下来,大部分绑鸡毛掸子,最好看的给我做鸡毛毽子。父亲做的毽子最好,先用花布包两块字钱缝结实,再把鹅毛筒剪二寸多长,底部半寸处剪开四瓣,均匀分开牢牢地缝在包字钱的布中心,把漂亮的鸡毛插满鹅毛筒,轻重恰当,穿着大棉鞋踢起,毽子翻飞,鸡毛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
想想这些,虽然都是三十多前的事了,繁忙而快乐,可年味十足。
后来我们都结婚成家,姑奶奶家,姑家们的亲戚也就退居二线了。初二初三是我们回娘家大团聚的日子。姐姐家哥哥家全都聚在父母的小院里,偎着父母热热闹闹的唠家常,说道说道各家一年的状况。吃饭时两三桌挤得满满当当,没有板凳就蹲着站着,筷子不够折根秫秸莛子,全是亲人,不在乎饭菜优劣,吃饱就行,见面就好。所有人都是幸福的开心的。
父母亲是最喜欢这样的场面的,看着眼前一大群孙子辈的孩子们一年年长大,脸上笑开了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父亲去世后,母亲离开小院去哥哥家住,也不再繁忙地准备各种年货了。近几年三个哥哥家的女儿们也都结婚有了孩子,她们成了年后回家聚餐的主角。我和姐姐们也慢慢成了娘家的远客,再也不在父母的小院里聚餐了。小院荒废了,我的心也荒废了。
文丨李艳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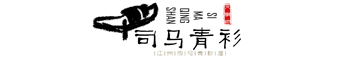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