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
《朱子语类》上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这代表着朱熹对孔子的评价。继孔子之后一千六百年,朱熹是又一位可比仲尼的大儒,故全祖望言朱子学云:“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这位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人类文化史中最珍贵的思想遗产。朱熹理学自13世纪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其地位与在中国同,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实源于此。有关朱子之学在东亚的具体传播,学界考备颇详,本文不拟赘述。至于朱熹哲学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论著不多,篇轶有限,知者更少。但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惟有从其对欧洲主流哲学的楔入和影响中方能体现。本文仅划一概要,难窥全豹,权作资讯,以飨同仁。
一、朱熹时代的中欧哲学大势之比较
朱熹(1130-1200)在世之日,黑暗的欧洲正处于思想剧变、“一佛出世”的前夜,即将来临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即恩格斯所说那个被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德国人称之为“宗教改革”、意大利人称之为“五百年代”的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自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社会便逐渐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迎来了近代文明的曙光。反观当时的中国,虽沐浴着汉唐文明的浩荡东风,但自唐朝中期始,已有人感叹孔孟之道失坠、古学不兴了。究其原因,归之于浮屠之教流行乱了中华学脉。于是,有韩愈著《原道》、《原性》,李翱著《复性书》,宣称自孟子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不传”,而韩李决意遥契孟子,接续道统,承传圣人之学,所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原道》)。朱熹认为韩愈还不够这个资格,推崇二程“实继孔孟不传之统”。作为二程的私淑弟子,欲做孔孟的嫡派传人,朱熹是当仁不让的了。
朱子之学果然集理学之大成而独树一帜,其博大、精深、细微和富有思辨的特点在当时世界上无人可比。12世纪的欧洲除教父哲学占主导地位之外,值得一提的只有二个人,那就是与朱熹同时的阿拉伯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和阿拉伯化了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斯(1135-1204)。此二人是最早把亚里士多德介绍给欧洲的非基督教学者,其主要贡献就在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罗素说:“阿拉伯人在哲学上作为注疏家,要比作为创造性的思想更优越。……唯有他们(而不是基督徒)才是只有在东罗马帝国保存下来了的那些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人。”他们使“希腊文明传布到回教徒的手里,又从回教徒的手里传至西欧。”恩格斯也说过:“在罗曼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由于希腊哲学本是湮埋数百年后重新被挖掘出来的,加之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波斯人的注疏与阐释,再几经传抄,已不可能保留一成不变的原貌了。就像中国古籍中不乏伪书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许多篇章的真实性早就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怀疑,如《论灵魂》更像阿维罗伊本人的作品,《论宇宙》等13种著作已被学者们证明为伪书。作为享有解释希腊“专利权”的阿拉伯和犹太的注疏家们,其创造性的劳动就在这些注疏里。在把希腊先哲们的遗著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字转化过程中,阿拉伯思想、东方意识不可避免地夹杂在其间。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丹皮尔就认为希腊哲学最有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因为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二转手。而另一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则认为宋代理学可能通过阿维罗伊和迈蒙尼德斯之手最早融进西方思想的发展序列中的。这二位学者都没有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实证,其结论往往建立在推理之上。丹皮尔的逻辑是:印度思想通过小亚细亚半岛的各学术流派(希腊哲学正是起源于小亚细亚的泰勒斯学派)进入希腊后融变成希腊哲学,但后人反而把印度给遗忘了。就像印度数字传到欧洲后取代了笨拙的罗马数字,后人却“把这种数码的发祥地忘得一干二净,反而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了。
不过,李约瑟所说朱熹理学被阿拉伯学者西传欧洲的那种情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阿维罗伊早朱熹二年逝世,迈蒙尼德斯晚朱熹四年去世,朱熹死后九年才得以平反昭雪,朱子之学流布天下,那更是以后的事了,绝不会在他生时就传到了遥远的欧洲。李约瑟如果指的是原始儒学、《易经》、道家或禅宗的思想,则可能性较大。
我们可以不去考虑当时中欧之间有什么实质上的学术联系,但要注意到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确有一人可跟中国的朱熹相比,这就是在朱熹去世24年后出生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朱熹和他是两位活跃在12世纪和13世纪东西方思想舞台上的大哲,其历史地位有颇多相似之处:
1、二人哲学的历史地位相似。阿奎那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吸收创立了经院哲学体系,他用理性神学取代了基督教的启示神学,如果剥去“经院”和“神学”的外衣,在希腊哲学湮埋了至少六百年后,是他第一个在神学的框架内开始复兴了希腊的理性精神。或者如罗素所言,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阿奎那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超过后来的康德和黑格尔。
朱熹继承了唐代韩李学派以来的“辟佛老,复孔孟”的传统,吸取了道家和佛家的思辨哲学,创立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庞大、最精深的新儒学体系,不仅恢复了儒家的道统,且统领了各派义理,开创了其后八百年的中国哲学和学术思想史,成为中国历史上自孔子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准确地说,中国哲学只是到了朱熹那里才有了真正完备的形态,其在中国的历史地位跟阿奎那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大致相当。
相比欧洲人不得不拜阿拉伯人、犹太人乃至波斯人为师才得以重建他们的传统的经历,儒家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不曾中断。然而朱熹创造性地利用道、佛两家哲理对儒家的阐释,不谛是一次对儒学的重新发现,后来美国人卜德把宋代理学译成“新儒学”(Neo-Confucians),便悟中了这个道理。
2、二人哲学的社会功用相似。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论证上帝的存在,使上帝的存在不仅成为真理,而且成为最高的第一真理,成为一切现存事物的“总形式”和“终极目的”。在关于一般和个别或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上,阿奎那强调一般先于个别、高于个别,从而推出神学高于哲学、信仰高于知识、神权高于政权的结论,这就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教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建立了一个逻辑上自足的理论体系,阿奎那本人和被他利用了的亚里士多德遂也升格为基督教的圣人和欧洲统治思想的化身;朱熹的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同样的功用,他集孔子以来一千八百年间儒、释、道三学之大成,在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树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理”。理先于一切,高于一切,成为现实皇权的精神象征,它为现实的封建秩序“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朱子全书序》),因此,朱熹哲学自1209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七百一十年间,尤其自1313年元仁宗诏告天下以朱注《四书》科考取士的六百年间,朱熹及其理学被奉为一尊,居于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
3、二人的遭遇相似。朱熹18岁中进士,一生只做过十年官,四十余年都从事讲学和著述。阿奎那没有朱熹长寿,只活了49岁,28岁获博士学位,一生从事于教授、著述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工作。然而此二人生前并不为官方承认,朱熹屡受贬抑,其学被诬为“伪学”,其人被辱为“伪师”,直到他死前,朝廷还下诏指责朱学门人为“逆党”和“伪邪之徒”,致使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直到朱熹死后九年,至宁宗时才得以恢复名誉,谥“朱文公”。阿奎那生前身后一直受到基督教正统神学家们的指责,尤其他那推崇亚里士德和阿维罗伊、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的经院哲学,被斥为“异端”,他本人也被视为基督教的叛逆,其学说不仅受到来自基督教内部的遣责,还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严厉批判。直至1323年,阿奎那才被教皇封为圣徒,又过了550多年(1879年),罗马教皇终于下诏全面褒奖阿奎那的神学和哲学。
4、阿奎那身后欧洲经院哲学内部分化为“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跟朱熹身后宋明理学内部的“道器”、“心物”之辩也颇为相似。这种争辨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深化了东西方哲学的思辨向度,促进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形成。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朱熹哲学与托马斯·阿奎那哲学都具有“继绝学”、“开来世”的特征,两相比较,可互衬出二者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崇高位置。当然,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一旦被统治者作为统治意志加以利用,最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僵化,走向它的反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古人。随着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西方文化在近代的强势崛起,托马斯·阿奎那已成为世界级的思想伟人。朱熹似只能被看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位先贤,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这对朱熹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二、朱熹理学与欧洲近代哲学
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毕竟是在神学笼罩下的哲学,其呆板、机械和形式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成为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进步思想的桎梏。正是在批判经院神学和呼唤“理性”的声浪日益趋高的启蒙思潮中,欧洲思想界迎来了中国哲学。
朱熹哲学是在文艺复兴后期至法国启蒙运动期间被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早在16世纪末,利玛窦就把朱注《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传到了欧洲。至17世纪,经传教士之手翻译成欧洲文字的中国典籍越来越多,其中以介绍儒家学说的书为主。那些以孔子名义出版的各类汉学书籍,由于时代的原因,几乎都打上了新儒学即朱熹理学的烙印。除朱注《四书》之外,一部影响最大的儒学著作是比利时神父柏应理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是一本系统向欧洲介绍儒家学说的读物,其导言名为《中国哲学解说》,其中介绍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可以说,当时在欧洲传播的儒家学说,名义上是孔孟之道,实际上是朱子之学。
如果说托马斯·阿奎那恢复希腊理性哲学需要披着神学外衣且必须为神学目的服务的话,那么,在欧洲真正抛开神学系统复兴了希腊理性哲学的第一人当推法国人笛卡儿。笛卡儿不仅是近代欧洲哲学开创山门的人,而且是真正历史意义上的欧洲第一位哲学家(因为希腊哲学实际上源于12至13世纪的阿拉伯人)。19世纪的欧洲学者即持有这种观点。如孔德就把全部欧洲思想史划为三个阶段,笛卡儿之前是“神学时代”,到了笛卡儿才进入了“哲学时代”,而孔德所处的19世纪则进入了“科学时代”。如果说中国的“哲学时代”从朱熹算起的话,欧洲的“哲学时代”则要晚了五百年。笛卡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和欧洲在精神层面上进入实质性交流的时代,“中学”开始西传,欧洲从此接触到了来自中国的哲学。由于笛卡儿生活在荷兰,所以笛卡儿学派的人物多是荷兰人和法国人,如斯宾诺莎、培尔和马勒伯朗士等。朱熹哲学在法国和荷兰的接引者是笛卡儿学派,在德国则有17世纪的莱布尼茨学派。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7至18世纪欧洲的几种哲学新论,不难发现朱熹哲学影响的鲜明痕迹。
(一)自然神论
17世纪以来,英法等国流行着“自然神论”,这跟朱熹哲学的传入密不可分。在朱熹那里,“理”具有先验性、超时空性、生物性和主宰性,它为自然和社会立法,但却不是人格化的上帝。“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有理在那里”“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理”的这种特性,在斯宾诺莎那里就是“实体”,也就是“自然神”。“自然神”是当时欧洲进步哲学家对上帝(神)不敢否认的一种否认,不敢反抗的一种反抗,是隐蔽的无神论,所以又称为“理神论”。莱布尼茨在其《论中国哲学》一文中,就明确提到《朱子》这本书表明了“中国人的理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名称之下所崇拜的至上实体”,“书名为《朱子》的第28卷关于哲学第13页的一段。著者说得非常好:心非气,而气之力。……我想象他的意思是要说:理(姑且这样说)是万物的精华、精力、力量和主要的体,因为他特意把理同气的物质区别开了,在这里好象不意味着原始的精神实体,而是一般地意味着精神实体或隐得来希,即象灵魂那样具有始动性和知觉或行动的规范的能力。”应该说,莱布尼茨对朱熹“理”的理解不脱欧洲文化的背景和欧洲哲学的话语传统,“‘理’是一般的精神实体或“隐得来希”即灵魂”――如果抛开朱子影响的背景,把这句话再翻回汉语,那就是标准的欧式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了――不了解其背景的人,肯定不会想到其中有朱熹哲学的影子。
在谈到朱熹的鬼神观时,莱布尼茨写道:“《朱子》第28卷第2页问:‘这些鬼神是气吗?’他答道:‘它们与其是气本身,还不说是气中有力、活力、主动性。’”“这位中国哲学家在第39页上说,天上的鬼神即天上的的帝王叫做神,因为天上的气到处扩散。”“中国人不相信天上有任何生命,有智慧的神,只相信有气,它有主动性或作用。”“中国作者给予神的不仅是力量或主动性,而且还有智慧,因为神让人畏惧、崇敬。把气――即希薄的物体――看作是神的载物体。……鬼神只不过是气、物质。”“我认为(总的来说),他们古代圣贤的意图是尊敬理或至上的理性。理及其作用到处可见,有时直接在粗笨的物体中,理在这些物体中是这些物体的创造者;有时表现为理本身的使者即下级鬼神,有德性的灵魂就结合在鬼神之上。”这显然已是一种地道的欧化的泛神论或自然神论的观点了。由于莱布尼茨本人是个有神论者,用这种自然神论解读出的朱熹可缓解有神论跟无神论之间的紧张。
笛卡儿提出了一些关于神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沉思,斯宾诺莎炮制了一个物质化了的神,在正统神学家看来那根本就不是神,所以斯宾诺莎学派到处受到迫害。莱布尼茨虽然是个有神论者,但他跟斯宾诺莎私交非浅,直接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斯宾诺莎本人跟中国哲学有着难解的谜底,这不仅因为他的实体一元论在欧洲哲学史上是个特例,被认为源于东方传统(康德则直接说它来源于《老子》的“道”),而且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位家庭教师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当黑格尔指责他抛弃了笛卡儿体系中的二元论,表现了一种“东方的余风流韵”,是“东方的绝对统一观被他纳入了欧洲的思想方式,特别是欧洲的哲学,尤其是直接纳入了笛卡儿的哲学”的时候,黑格尔则以“头足倒置”的手法吸收了斯宾诺莎的一元“实体”论,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也表现为一种自然神论,而且是最高形态的自然神论,被马克思称作是“理性的神学”。
由于受中世纪的影响,“无神论”在欧洲是个贬义词,而“自然神论”则是进步思想家用以反教会、批判有神论的思想武器。当有人把朱熹理学作为宣传无神论的异端加以贬斥时,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的泰斗伏尔泰则极力为中国哲学辩护,伏尔泰写道:“人们曾认为中国的儒生对无形的上帝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由此推论他们不信神有欠公允。……古代所有的神都以人形受人礼拜的,因此希腊人把那些不承认有形之神而奉不认识的、不可感知的自然物为神的人斥为无神论者。(与对待中国人态度比较起来)这清楚地表明世人是何等的不公平了。”伏尔泰接着又写道:“我们诬蔑中国人,仅仅因为他们的玄学不是我们的玄学,其实我们应赞赏中国人的两点长处:既遣责异教徒的迷信,也遣责基督徒的习惯作法。中国儒生的宗教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也没有为政教之争和内战所玷污。”③这分明是在为朱熹的“自然神论”即实质上的无神论唱赞歌了,并以此作为他在法国从事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
(二)有机论哲学
李约瑟曾指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所谓“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在朱熹之前,中国哲学的全部背景都是如此,在朱熹之后,则有莱布尼茨的哲学。“有机哲学”不是常用哲学术语,它是李约瑟爱使用的概念。有机是相对于无机而言,从生物学名词“有机体”和“无机体”借鉴而来。“无机体”是无生命的物体,“有机体”是有生命的物体。有机哲学指有生命力的哲学,即贯穿着辩证思维方式的哲学体系,也即普遍联系的、能动的、发展的、变化的,并在对立和矛盾中达到平衡和统一的宇宙观。简言之,有机哲学就是辩证辩证唯物论。但在欧洲的哲学传统中,向来是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占统治地位,尤其13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奉为圭臬,加之牛顿力学引发的机械唯物主义,使得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无人问津了。而莱布尼茨哲学的“前定的和谐”命题,确是自笛卡儿以来的第一个辩证法命题,李约瑟指出,它来源于莱布尼茨对朱熹的研究,“他(莱布尼茨)的‘预先建立的’和谐说(虽然是用有神论者的词汇写的,但这是当时欧洲环境所必需的),在那些熟谙中国宇宙观的人,便觉得不陌生。万物之间,皆不相互施行作用,它们只在一个和谐的意志下共同活动。此种思想对中国人已不是什么新观念……”
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是指精神性的实体“单子”具有能动性,“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单子,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单子没有“窗户”,没有东西能从里面出来或从外面进去,单子跟单子之间按自己“前定”的本性发展而万物之间就自然彼此合拍与“和谐”,仿佛彼此互相作用或互相影响似的,整个世界的单子就是这样普遍联系、相互协调一致而达到动态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前定和谐”。莱布尼茨还说:“能动性是一般实体的本质”,“在自然的情况下,一个实体不能没有行动,甚至没有一个形体没有运动。”这跟朱熹对“理”、“气”和“太极”的描写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如朱熹说:“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则未尝相离也。”“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李约瑟指出,正是朱熹的这种思想影响了莱布尼茨,使莱布尼茨成为第一个创立“有机哲学”体系的欧洲哲学家。
“有机哲学”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莱布尼茨的敬佩,列宁也曾指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直接受益于莱布尼茨,同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直接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在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然而康德的“星云假说”实质上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有机论的自然观”,它跟朱熹的有机论宇宙观没有什么两样。
所谓的“星云假说”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假说”;第二,它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的宇宙生成观”。所谓“假说”,“‘假说’在西方哲学中原是没有的,而在中国‘假说’这种概念最早见于《墨经·小取》:‘假者,今不然也。’这里的‘假者’就是‘假说’。”所谓“有机论的宇宙生成观”,本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在道家哲学和古代天文学中就存在着的一种假说,到了朱熹那里则表述的更为清晰。朱熹说:“天地初开,只有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去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去,便结成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他明确反对“神创说”,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而康德在其巨著《宇宙发展概论》中开宗明义就表明他的宇宙学说就是“要在整个无穷无尽的范畴内发现把宇宙各个巨大部分联系起来的系统性,要运用力学定律从大自然的原始状态中探讨天体本身的形成及其运动的起源。”这无论在目的、方法和“假说”本身,都与朱熹的有机论完全一致。
至于康德的辩证法――“二律背反”的思想,则直接继承了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而莱布尼茨的“二元算术”又跟朱熹和邵雍的《易》学系统相关。正是这种“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辩证法到了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顶峰。我曾经比较过黑格尔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之间的同异,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纳入了欧洲的思维形式”之中,采用了欧洲的话语传统,并且在黑格尔那里确实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盈和发展,但其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即不是赫拉克利特的)。这个基本原则在宋代理学那里已经非常完善,源头就根植在《易经》哲学体系中,而恰恰是《易经》这本书受到了黑格尔极高的评价,黑格尔认为它是一本“论原则的书”,代表着“中国科学的最高智慧”。
(三)纯粹理性
在17世纪的欧洲,笛卡儿学派得风气之先,后来伏尔泰又把英国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引进了法国,由于牛顿实验科学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笛卡儿的崇拜,风向开始转向了英国。但英法两国在哲学上的脉络,最后都在德国哲学园地里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康德受到过休谟的影响,黑格尔哲学受到斯宾诺莎学派的影响,但黑格尔哲学则直接继承了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到康德所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换言之,黑格尔不仅是莱布尼茨以来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笛卡儿以来欧洲哲学的集大成者。
莱布尼茨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哲学,直到他逝世前一年还在询问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他的学生沃尔弗继承了他的事业,对中国哲学十分推崇,曾在就职哈勒大学校长职务的典礼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实践哲学》一文。“实践哲学”这一名词源出于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中指的是道德哲学。最早用“实践理性”、“实践哲学”来称谓中国哲学的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康德是沃尔弗的学生舒尔茨的学生,是莱布尼茨正宗的三传弟子,虽然他在创立其哲学体系中接受了法国卢梭和英国休谟的影响,但不失莱布尼茨嫡派和真传的身份。
为什么哲学史上把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而不是莱布尼茨呢?据我个人的体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以“先验的”、“纯粹的”、“道德的”理性为主轴建立哲学体系(“三大理性批判”)的人,在康德之前尚未有过,这标志着康德在整个人类思想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完成了思想史上的一项前无古人的哲学革命,其成就和历史地位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师辈们;第二,康德是第一个全部用德文写作的哲学家,然而在他之前,包括莱布尼茨和沃尔弗等德国哲学家都用拉丁文写作,所以,康德是一个真正属于德国文化的思想巨匠。由于这两大原因,把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者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德国只是到了18世纪才有了自己民族的哲学,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
康德哲学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跟中国哲学都有着难解之缘。这不仅是因为康德哲学源出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尽管他曾表示要从莱布尼茨的“独断论”中“觉醒”,但他从莱布尼茨学派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却十分丰厚,其中包括潜移默化的中国哲学要素,况且他本人也直接阅读和研究过中国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康德哲学太像中国哲学了,所以尼采称他是“哥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人”。我们已经指出了康德的宇宙生成论跟朱熹的有机发生论在原理上一致,而当我们剖析他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时,我们发现他跟朱熹的“理”或“太极”更为相似,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理性的先验性和至上性、道德的形而上性和实践的自律性以及“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朱熹的“理”传入西方之后,一直被欧洲哲学界看成是取代上帝的“纯粹理性”。如谢林就指出:“我们一定能够――以便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找到一种上帝的替代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原始神明的替代物。”“经过宗教原则的彻底转变和市俗化,中国人的意识完全避开了宗教过程,并在一开始即达到了其他民族经过神话过程才能达到的纯理性的境地。”欧洲人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才认识到了“纯粹理性”的存在,而中国却很早就达到了这个境界。耶稣会士在翻译朱熹的“理”时,最早使用了“理性”(Reason)这个字眼。近代欧洲哲学上的“理性”概念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希腊,其二是中国。朱谦之先生说:“……理性的观念是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希腊来的呢?我可以肯定的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因为希腊的“理性”,更多地是用Nous或Logos这个词,而朱熹的“理”一直是用的Reason这个词,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所呼吁的理性,不是Nous,而恰是Reason。这还可以从黑格尔的话中得到验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在中国有一个哲学体系,从中可以看到纯粹抽象的一元和二元观念,似乎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相同的出发点,“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黑格尔每当提到中国哲学的“理”和“道”时,都是用“理性”(Reason)这个词,并用“合理”与“非合理”解读和分析它。
中外不少学者在其著述中指出了朱熹“理”的传入对18世纪法国“理性时代”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法国,最先提倡“理性”(Reason)的哲学家是笛卡儿,所以笛卡儿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先驱”;而极力提倡“理性”的思想家是伏尔泰,所以伏尔泰被称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又是法国宣传中国文化的重镇,他理解的“理性”便是来自朱熹的“理”。此外还有重农学派的首领魁柰和百科全书派,他们都十分推崇中国的“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即“无神论”或“唯物论”,如笛卡儿学派怀疑主义的重要代表培尔坚持认为中国哲学就是“无神论哲学”、断言中国社会是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无神论社会”。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性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清一色的无神者所组成的社会”就是接着培尔的话说的,就是指的中国。笛卡儿学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马勒伯朗士写了一篇《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学者的对话》的冗长文章,对话中的一方“基督教学者”可视为马勒伯朗士本人,对话中的另一方“中国哲学家”实为朱熹的的化身。马勒伯朗士把中国哲学的“理”界定为无神论,从而反对把“理”说成是“上帝”。“理”是离不开物质的(朱熹曾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也未有无气之理。”),马勒伯朗士指出这种一方面把“理”说成是先验的最高原则,另一方面又把它混同于物的观点,实际上把“理”变成了可灭的东西,这种思想远离了天主教神、物二分的原则。其实朱熹也说过“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理”是永不消失的,所以有人指责马勒伯朗士不得中国哲学要领。但马勒伯朗士对朱熹“理”的定性认识实比耶稣会士把“理”比拟为“上帝”的做法更能接近朱熹“理”的本色,即“理”“气”的不可分性。马勒伯朗士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所以在18世纪欧洲,变成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变成革命的哲学,这一位笛卡儿中派的麦尔伯兰基(马勒伯朗士)的解释,对于法国百科全书派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四)绝对理念
“绝对理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它的提出有着自笛卡儿、斯宾诺莎以来深厚的欧洲近代哲学基础,尤其有着自莱布尼茨以来德国经典哲学的土壤。
对于不熟悉朱熹哲学的欧洲人,他们一度读不懂莱布尼茨的“单子”,总认为它是神秘论。但读过朱熹之后,疑虑便迎刃而解了。莱布尼茨在分析了朱熹“理”跟“气”的一些基本特征之后曾经指出:“这里的‘理’似是不指第一类精神实体而指普通的精神体或单子。”“单子”就是“理”,而“理”也就是“单子”。“单子”只不过是赋予了莱布尼茨以个性化色彩或“形而上学改了装”的“理”而已。至于康德先验论的“理性”哲学跟朱熹哲学之“同”,已无需多证了。尼采说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毛泽东早年也说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当然这种“同”不是绝对地等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果康德时代朱熹哲学没有传到西方去,我们只把两个孤立的个案进行比较,再论“同”与“异”,那就不能说谁影响了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从莱布尼茨以后,德国哲学家往往就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来称谓和解读中国哲学的“理”,康德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抹去这一时代“中国哲学热”影响的痕迹。同样,对待黑格尔“绝对理念”这一范畴,我们也只能看成是在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基础上的新发展,而朱熹的“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要清除“西学中源说”的狂大心态,更要清除“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禁锢。正如楼宇烈、张西平先生所说:“自传教士来华以后,中国文化已成为西方近代文化形成重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这点恐怕大多数从事西方近代思想研究的中国学者还尚未认识到。”
剔析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对认识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最有意义。如果我们把黑格尔与朱熹作为孤立的个案进行比较学的研究,不会有人反对。但如果我们要说:黑格尔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坚决否认这一说法,甚至会指责我们散布“西学东源说”。理由很简单:作为西方主义肇始者的黑格尔,如此那般轻视中国哲学,怎么可能接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呢?孰不知,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从文化发生学的立场来看,国际学术界采用的是“一元发生论”标准,如:全世界的人种都起源于非洲,中国人也不例外,这就是一元发生论的最典型的代表观点。就某一学科、某一理论来说也是如此。判断两个科学发现或理论新说之间彼此有无影响,取次于三个标准:1、看二者有无先后或谁者在先;2、看后者是否对前者有无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接触;3、看后者的成果是否包含前者的形式和内容,哪怕是局部或部分。从这三点出发,作为后来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无法排除受其前者中国哲学之影响的。当然,后者对前者不可能是单纯的“克隆”,总会有修改、变异、损益和发展的。
首先,黑格尔的时代,中国哲学已在欧洲传播了二百年,这二百年间其在欧洲文化中的沉淀和对欧洲思想界的渗透,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哲学欧洲化的转换,如莱布尼茨和康德等人的哲学。其次,黑格尔本人直接研究过中国哲学的资料,“他曾研究过当时译成西文的中国各种经籍,阅读过13大本被称为中国皇帝的通鉴,朱熹著的《通鉴纲目》,读过耶稣会士所搜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丛刊》,利用过法国学者亚培·累蒙萨和圣·马丁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访中国的记录,甚至19世纪前期才在欧洲出现英译本的中国小说《玉娇梨》等,黑格尔对前人的中国文化观也是熟悉的,他深知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是再往前的中西交通史也了解。”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哲学经典《周易》、《论语》、《老子》及全部的朱注《四书》和《五经》,他都阅读并研究过。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也能发觉到。黑格尔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一味贬低中国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褒扬和肯定的成分多于贬损和否定,唯一的例外是对孔子的态度。黑格尔所受到中国哲学的这种直接影响,已为不少国外学者所注意,如威泰福格尔说:“黑格尔凭借着这种巨大的参改材料,自己感觉有了不少的知识上的培养,我们现在确实已十分认识中国了。我们已有了中国文学和它的全部生活,以至它的历史之深切的知识。”
第三,黑格尔哲学中明显地含有中国哲学尤其是朱熹理学的成分。贺麟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朱熹之“理”或“太极”,张岱年先生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东西,它跟柏拉图的“理念”不是一回事,而跟朱熹的“理在气先、寓理于气”之“理”、“理一分殊”之“理”实在太像了。有趣的是,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外国人,这就是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我曾经在拙著中引用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批评者也不好随意曲解马克思的原意,但总觉得马克思对中国哲学说得太少了。少固然是少了点,但透露出的信息量何其大矣!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不仅吸收了古代希腊和近代欧洲的哲学成果,而且吸收了东方哲学主要是儒学和佛学的思想成果。对此,马克思也有高论,他说:“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
这段话是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时所阐发的。此处所说的“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指的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章。中国的“有”即当时欧洲普遍认定的中国哲学的唯物论哲学或朱熹理学,而印度的“无”则指源于印度佛教的唯心论哲学,在当时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禅宗。马克思一直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对前辈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统一”或“形而上学的改装”,如他在另一处写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这段话的句式和表达的意蕴跟上一段完全相同。不过,此处中国哲学的“有”变成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而佛教哲学的“无”换成了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正是“有”与“无”、“实体”与“意识”的统一。作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解是正确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所包含的中国哲学因素是不可否认的。
三、朱熹与马克思
说完了黑格尔,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活动的时代是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那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退潮,西方主义甚嚣尘上。然而,身为黑格尔的学生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继承者,在马克思所接受的哲学遗产中无法剔除已经被内在地消化吸收了的中国哲学成分。当然,这可以算是一种间接的来源。无论是16世纪传来的中国哲学还是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距马克思的时代都不远,其余风流韵漫至19世纪,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对中国哲学的直接吸收。例如,从上文已经引用的马克思论黑格尔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两段话中,我们即可得出:如果马克思没有研究过中国哲学,他就不可能把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进行比较。实际上,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间接还是直接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都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早有人这样提出来了。
大约半个世纪前,李约瑟先生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认为中国的儒学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类似之处。持这一观点的,在西方大有人在,此处无需一一列出。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李约瑟先生还大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虽然李约瑟的言论受到一批时贤们的强烈批评,但许多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十分赞同。如中国学者孙叔平、张岱年、匡亚明等人就表示过:当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郭沫若在“五四”之后写的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文,文中把马克思写成了孔夫子的学生,惟妙惟肖地构画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文化心态上对马克思的认同。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元帅就公开表示过:他之所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据窦宗仪先生说,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越南学者中十分普遍。⑤
如何来解释这种思想文化现象呢?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还是旁观者清。作为一个旁观者和最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李约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⑥李约瑟的这番理论从郭沫若那里可以得到证实,郭沫若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可见,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开花、结果,决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总之,自从以朱熹理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于16世纪传入欧洲之后,正合了欧洲复兴“理性主义”的历史符节,从而作为助力推动了欧洲进入了“哲学时代”或“理性时代”。此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建,朱熹的理学都起到了导索和酵母的作用,以至于融贯于欧洲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思想来源和资料。无论从朱熹在中国和东亚相当于托马斯·阿奎那在西欧的历史作用来看,还是从朱熹哲学传入欧洲后对欧洲哲学发展的贡献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流的世界级思想家,其实际作用不在任何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之下。我们今天充分挖掘和认识朱熹哲学的这种世界历史作用,对于中国社会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凝聚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豪迈地走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文/玄儒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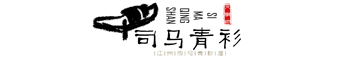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