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三义庙前松涛飒飒,林中的猫头鹰不时发出瘆人的叫声,更增添了令人恐惧的气氛。一个和尚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四下里踅摸了一阵子,随后关好山门,飞快地朝后边的僧房中跑去。
宽敞的僧房里,和尚们早已摆好了酒菜。老和尚“尤鹏”坐在正中,这个老和尚,正是沿河镇山西会馆的掌柜的。难怪化妆侦查的警察署长马剑飞在庙里见到他时觉得有些面熟,二人在沿河镇时虽然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也免不了有碰面的时候。马剑飞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看上去待人十分谦和的山西会馆的大掌柜的,其实正是个心黑手很的土匪头子。
此时,尤鹏手下的二十多个土匪,却还是僧人打扮。只有两个从山下的山西会馆跟来的伙计,依旧是一身俗家的便装,在席间反倒显得十分扎眼。
老和尚尤鹏端起一碗酒,站起身来眉飞色舞地对众人说:“弟兄们,前几天咱们劫下的那口棺材里,装着整整的八千两黄金哪!弟兄们,咱这回……可他妈发了大财啦!咱就是现在就下山去,住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里,一天换一个娘们儿,这辈子也他妈花不完哪!哈……”
众匪也跟着大笑起来,七嘴八舌地吵吵开了:“老大,你当初是咋盯上这只肥羊的?”
一个在山西会馆当伙计的家伙抢着说道:“咱老大是干啥的?五黄六月的,谁会在这日子口儿往家运尸首?搭眼一看就他妈的不地道。”
另一个爱抬杠的土匪嘴里不以为然地发出了一声“嘁”,随后走到那小子跟前,喷着老高的吐沫星子接着说道:“照你说,死人都得搁在十冬腊月再往家里运呗?”
周围的人“轰”地一声都笑了。
在山西会馆当伙计的那小子把眼一瞪,说道:“你知道个屁!这人要是死在了夏天,一时半会儿又运不回老家去;咋整?那就得先把尸首先入了殓,然后再把棺材连同里面的尸首‘停厝’在一个地界儿,等到秋凉了以后,再拉着棺材上路。要是大夏天的就抬着棺材上路,嘿——,瞧着吧,那股味儿谁他妈受得了?走不了多远那棺材就他妈得流汤儿啦!”
众匪又大笑起来……
在山西会馆当伙计的那小子接着说:“那几个小子赶着大车一进咱山西会馆的大门儿,可就犯了‘忌讳’。大夏天的千里运尸首,准他妈有病啊!咱老大打眼一看,就他妈看出来了:那几个小子都他妈是‘练家子’,一个个走道都端着架势,俩脚全是外八字。又何况,既是扶柩还乡,怎么会没有一个戴孝的秦人呢?没有近亲的人在场,谁敢把死者入殓?除非那是个家里都他妈死光了的‘老绝户’!咱老大当时就看出来了:他那棺材里边有‘货’。江湖上早就有规矩:押镖上路的镖师,有走‘明镖’、‘暗镖’之分。一般来说,凡是押运那些见不得人的货物,特别怕别人发现、检查的,才他妈走‘暗镖’。咱老大晚上特意安排我一试探,我他妈上了房顶儿,刚往那口棺材上扔了一块瓦片儿,旁边的车里立刻就跳出俩小子,亮开手里明晃晃的钢刀,列开架势,准备拼命。要是那棺材里真的装的是死人的尸首,还他妈用得着派人看着吗?探听得棺材里确实‘有货’,老大这才派我连夜上了山,叫上哥儿几个,下山牵了这头‘肥羊’。哈……”
众匪徒也拍手大笑起来。
一个土匪急不可待地说:“老大,我他妈的早在山上呆腻了。干脆咱明天就他妈下山去,到八大胡同去找娘们呀——”
另一个土匪附和道:“对!我听说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里还有外国的洋娘们儿哩。咱也弄匹‘大洋马’骑骑,也他妈尝尝外国大娘们的滋味儿;哈……”
尤鹏抚撸着秃头,感慨地说:“老子干了一辈子,就等这一天哩。唉——,当初老子20多岁就在关外当胡子,混到今天不容易呀!那年,张作霖在奉天城摆酒请咱们爷们,还他娘的打铁岭请来一个唱‘蹦蹦戏’的草台班子。妈的,我凭啥侍候他?我他娘的吃了、喝了,娘们儿睡了,大洋搂足了,然后就给他来了个脚底下抹油,溜啦——”
众匪大笑起来。
尤鹏站起身来,一边蹓跶着,一边用手比划着接着说道:“唉呀,那回可把‘张老疙瘩’气坏了。后来我听说,张作霖下了死命令,说再见着我,不要活口。非要我尤某人的脑袋不可呀!妈的,说实话啊!张作霖是他妈比我厉害。我当时带着二百多人,钻进了老林子,让张作霖的骑兵追的是没处躲、没处藏啊!末了在关外实在呆不住了,我这才带着弟兄们进了关。一晃的功夫,咱们爷们儿占了这‘三义庙’也有十来年了。当初跟我一块儿拉杆子的弟兄们,如今就剩你们二十来个了。这可真他妈应了那句话:井上罐儿不离井上破,黄泉路上没老少哇……”说到伤心之处,尤鹏的五官都挪了位,俩眼使劲儿挤了半天,总算挤出两滴眼泪。
众匪徒七嘴八舌地骂道:“奶奶的,活一天就他妈得快活一天!”
“该死屌朝上,咱爷们儿活到今儿真不容易呀!”
尤鹏接着说:“弟兄们,咱们往后真的不能再趟‘黑道儿’了。我都这岁数了,这碗绿林饭还能再吃几天?还有一宗:为人一世,咱总不能混到百年之后,坟头儿前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吧?我盘算好了,咱们今天喝完这顿酒,你们再委屈几天,先下地洞里躲上一阵子。等这阵风儿过去,咱把钱一分,都他妈下山当财主去。咱他妈的拿这笔钱当本儿,也改行做买卖,然后也娶一堆媳妇儿,生他妈一窝孩子,哈……”
“老大,那还躲啥?咱明天就下山不行吗?”
尤鹏把脸一板,生气地说:“你懂个屁!你知道咱前几天劫的那八千两黄金是谁的吗?”
“奶奶的,就是皇上他二大爷咱也不怕!”
尤鹏压低了声音紧张地说:“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整明白:这笔钱是山西都督阎锡山购买军火的钱。那阎锡山……是好惹的吗?就连咱东北的张作霖张大帅,那也得让他三分哪!丢了这么一大笔钱,那阎老西儿能善罢甘休吗?没听说吗?山西老西儿,那可是有名的‘舍命不舍财’呀!为了这笔钱,闫老西儿非他妈跟咱们爷们儿拼命不可呀!”
众匪大吃一惊,都傻了眼。
老贼尤鹏倒背着手,在屋里蹓了几步,又接着说:“今天上庙里来的那个小子,正是沿河镇警察署署长马剑飞。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这小子原先是冯玉祥手下的连长,打仗时受了重伤,伤好之后,老冯写了二指宽的一个纸条儿,把他派在沿河镇当了警察署长。我在沿河镇见过他,可没跟他说过话。白天在庙里,他跟大爷我一通瞎白话,话里话外能听出来:他已经‘贼’上咱们爷们儿啦!这指不定是从哪儿漏了风,才把‘鬼’招上了山!咋着,明天下山?嘿嘿,人家早就他娘的布好了天罗地网等着咱哩,谁下山谁倒霉呀!”
众匪面面相觑,都吓坏啦!一刹那的沉寂之后,有人紧张地对老贼尤鹏说道:“老大,那……那咋整啊?”
尤鹏大大咧咧地说道:“慌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天晚上你们来个酒足饭饱,然后统统下地道。我一个人在上边儿支应着,我就不信我还斗不过他个龟孙子!”
有人紧张地问道:“老大,万一人家上山来,问你我们这些人都上哪儿了,你咋说呀?”
尤鹏说:“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下山给人家办丧事儿、念经去了。要不就说你们化缘去了,他有啥法?”
“老大,为啥非要我们下地道里躲着呀?”
尤鹏骂道:“你他妈还有脸问?今天白天在庙里,不是我拦着,你跟马剑飞那小子还不得打起来?你个鳖犊子……”
“那小子往咱的井口里看,我心里能不发毛吗?我怕他……”
老贼尤鹏说:“怕个屁!那口井十几丈深,从上边往下看,啥也看不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能折能弯方为好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过什么山唱什么歌。小子,你他妈的毛还嫩着哩,哈哈……”
那小子用手搔了搔头皮,笑着说:“可是……,我们在地道里待到啥时候呀?”
尤鹏想了想,说道:“多则半个月,少则三五天。弟兄们,过了这个坎儿,咱们就他娘的下山快活去啦!来,咱先干上它三大碗,喝——”说着话,老贼尤鹏端起碗,带头儿喝了下去。众匪也端起碗,狂饮起来……
一直喝到了到后半夜,老贼尤鹏才带着醉得东倒西歪的众匪,来到外面的井台儿上。众匪按着老和尚尤鹏的吩咐,一个个攀着辘轳上盘着的井绳,溜了下去。尤鹏阴险地笑着,不时催促着土匪们下井。匪徒们一个接一个地顺着井绳滑入井内。当最后一个土匪下到井里后,老贼尤鹏突然掏出匕首,一下子就割断了井绳……
尤鹏冲着井口儿狂笑起来,大声说道:“弟兄们,别怪我心黑手狠,实在是那八千两黄金太他妈让人眼红啦。老辈子人早就说过:绿林的哥们儿弟兄,能一块‘共患难’,可他妈的就是不能‘同安乐’。什么他妈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都是他奶奶的屁话!弟兄们,我会给你们烧纸的,咱们下辈子再见啵——”
尤鹏无意间一回头,发现自己身边儿的俩伙计正瞪大了惊恐的眼珠子,在看着他。老贼尤鹏转过身恶狠狠地说:“怎么,害怕了?这就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留着他们,早晚是他妈祸害。”
两个伙计赶忙跪在地上,给尤鹏磕着头。
尤鹏笑着说:“干啥?你们这是干啥?”
伙计甲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说:“尤爷……饶命啊!那笔外财,俺俩一个子儿也不要……”
伙计乙说:“尤爷,您…您要瞧着我别扭,我…我立马就滚蛋,永不在沿河镇再露面儿……”
尤鹏哈哈一笑,忙扶起二人,安慰道:“你们俩别怕,你们俩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个个都他妈的恶贯满盈,血债累累;早就该死了。我要放他们下山,他们狗改不了吃屎,还得给我招灾惹祸,早晚还得让人家给逮了去。警察逮了他们,能不牵连到咱们吗?留着他们,早晚是个祸害呀!你们俩是这二年才跟的我,一直在山西会馆当伙计,从没干过杀人的勾当,我把你们留在身边心里踏实。再说,我还要派你们去干大事儿哩。”说罢,尤鹏领着两个伙计回到方丈室,用力搬开地上的石板。两个伙计二次进入暗室内,将一个个装着金元宝的十分精致的小楠木匣子搬了上来。二人清点了数目,伙计甲点头哈腰地对尤鹏说:“尤爷,一共二十个楠木匣子;全在这儿。”
尤鹏走到跟前,用手打开最上面的一个木匣。只见匣内装着排列整齐的金元宝。尤鹏贪婪的目光紧盯着金元宝,发出了令人恐惧的笑声。接着,尤鹏把手一挥,大声说:“咱快下山去。”说罢,老贼便找来一把破笤帚,在蜡烛上点燃后,又将着了火的笤帚移到窗户前,点燃了木制的窗户。然后,尤鹏命二人抱起装着金元宝的楠木匣子,出了方丈室,吃力地朝庙门外走去。
三义庙里的木窗户最先着了,随后木窗户的火苗儿很快就烧着了房屋屋顶上的椽子,椽子又烧着了檩条、房梁、房柁。大殿的顶部烈焰腾空而起,风助火势,火仗风威;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整个儿三义庙顷刻间就成了一片火海,跳跃着的火焰把半边天都映红了。附近的鸟雀发出惊恐不安的叫声,此刻听来格外瘆人。
两个伙计找来扁担和绳索,把装着金元宝的楠木匣子捆绑结实,二人吃力地用扁担抬了起来。尤鹏拎着手枪跟在后面,三人顺着石阶,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山下走去……
到了山脚下,尤鹏招呼二人来到早就停放在那里的两辆大车前,先命人将装着黄金的小木匣整齐地码放在一辆大车上,伙计甲胆战心惊地快步跨上车辕,举起手上的鞭子,还没等鞭子落下来,尤鹏手上的枪就响了。伙计甲应声倒下,滚到了路旁的沟里,抽搐起来,很快就不动了。
尤鹏又用枪指着伙计乙,谁知,还没等他开口,伙计乙抬手对着尤鹏的面门就是一枪。尤鹏当时就把眼一闭,心里说:这下儿可他娘的完犊子啦!枪口离得太近了,根本躲不开呀!
然而,等了老半天,那小子的枪居然没打响。尤鹏再睁眼一看,只见那小子正在气急败坏地摆弄着手里的手枪。真是“天不灭曹”啊,那小子的枪,居然在节骨眼儿上突然卡了壳。尤鹏不敢怠慢,抬手对准那小子的脸就是一枪,紧接着又是一脚,就把那小子的尸首从车上踹了下去。随后他在黑暗中拼命地赶上那辆装着黄金的大车,发狂地朝沿河镇方向狂奔而去……
第二天天刚亮,准确地说,就在老贼尤鹏放火烧了三义庙之后的几个小时;沿河镇警察署长马剑飞,就带着从外县警察署借来的百十号警察,包围了宛平县和良乡县交界处的这座“三义庙”。面对还在冒着烟的断井颓垣、狼藉一片,马剑飞恨得牙根直痒。他断定:土匪们已经带着赃物逃跑啦!临走前又放了一把火,烧毁了三义庙,彻底毁灭了一切的罪证。他下令手下人对三义庙仔细搜查,结果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虽然有人在山脚下的山路上发现了血迹,但这血迹能说明什么?原本可以作为证据的死尸,早就被野兽拉扯走啦!再说发现血迹的地点离山上的三义庙太远了,自然也没有引起警察们的注意。马剑飞命人做了现场笔录,就垂头丧气地带人下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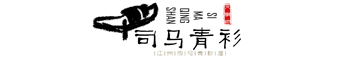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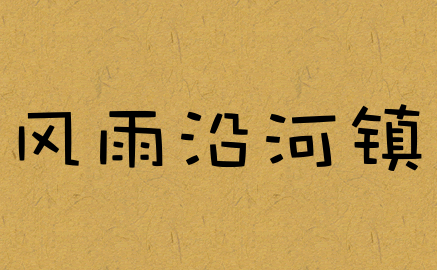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