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康家忙着大办丧事儿时,郝玉川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带着翠萍姑娘,在一辆装着荷枪持弹士兵的军用大卡车的护送下,也回到了沿河镇。
郝玉川没有回家,而是直接领着翠萍姑娘和这伙丘八们下了馆子。直到大兵们个个酒足饭饱,郝玉川又偷偷儿地给当官儿的手里塞足了钱,大兵们才心满意足地坐着汽车告辞了。打发了这些大兵之后,郝玉川这才带着翠萍姑娘,回到寿仙堂的家中。
高家父女见了面,免不了痛哭一场。当晚,高万祥坚持父女二人不能继续住在郝家了。于是,郝玉川便安排高家父女到“山西会馆”暂住。而此时,天真的翠萍姑娘还什么都不知道,她眨着美丽的大眼睛,不解地问道:“爹,咱住在寿仙堂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去住店呢?”
荷香夫人抿嘴一乐,拍了拍翠萍的肩膀,笑着说:“好妹妹,过几天再把你热热闹闹地接回来。怎么,你……等不了了吗?”
郝大夫听出妻子话里有“骨头”,立刻就涨红了脸,忙把脸扭向了一边。他一直没有告诉翠萍姑娘“要娶她为妾”的事儿,说不出口啊!
翠萍糊涂了,自言自语道:“这不是……瞎折腾吗?”
荷香夫人笑着说:“好妹妹,人哪,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怎么能说‘瞎折腾’呢?再怎么着,也得让你坐八抬大轿进这个家门呀!”
翠萍还是没听明白,刚要再问,高万祥忙用手一拉她,小声说:“傻丫头,别问了;回头爹跟你细说。”说罢,在众人的搀扶下,高万祥走出了房门,来到了街上。伙计们早就预备好了车,高家父女上了车,直奔了不远处的“山西会馆”。
郝大夫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迎娶翠萍姑娘的仪式办得漂漂亮亮,要像当初他娶夫人时一样,甚至比上次还要排场。他这么打算主要是冲着高老爷子的面上,人家可是一代武林大侠,非比常人哪!
郝玉川提前在山西会馆订了一个最好的套间房间,供高家父女居住。伙计们谁不巴结郝大夫?自打高家父女一到房中,几乎所有的伙计,都专门儿来为高老爷子来请了安。厨师也来了,仔细详细地询问了高家父女习惯的口味儿。
夜深人静之时,高万祥这才把女儿叫到跟前,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押镖被劫,七个徒弟命丧枪下,他自己身负重伤,幸被郝大夫救起的事。最后,他苦笑了一声,对女儿说:“翠萍,咱家在山西……是没法再待下去了。我受人家郝大夫那么大的恩惠,让我咋报答呢?思来想去,爹只有……”老爷子说到这儿,可就说不下去了。他偷眼看了看女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有谁能相信:堂堂的“通臂王”高万祥,会把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嫁给人作妾呢?实在太委屈女儿了。万一女儿不乐意可咋办?他能强逼女儿应允婚事吗?不能!他这一辈子,从来没跟幼年丧母的女儿大声说过话,事事都由着女儿的性子来。他怎么可能在这件“终身大事”上让女儿不遂心呢?老爷子着实犯了难。
可话又说回来了,他在人家郝大夫面前,可是答应这门儿亲事了。准确地说,还是他求的人家。难道让他在朋友面前失信?高万祥心里七上八下地翻腾着,彻底乱了方寸。
翠萍姑娘是何等的聪明?从小生在武术世家,她当然听说过“道儿”上的种种规矩。老父亲失了镖的严重后果,她完全清楚。父亲受了人家郝大夫的救命之恩,更是怎么报答都不过分。为了她的平安,人家郝大夫居然找来军车,专门儿请来一车荷枪持弹的大兵一路护送,专程去山西接她,这岂是一般的关系?荷香夫人说的那句“再怎么着,也得让你坐花轿进门”,她难道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前思后想,翠萍姑娘鼻子一酸,忍不住两行热泪滚落下来。为了不让父亲难过,她立刻背转身去,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珠儿,用颤抖的声音说:“爹,我……都听您的……”
“你……愿意……给郝大夫……做小?”
“我……我愿意。”话一出口,翠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用手蒙住脸,痛哭起来。
老侠高万祥忙上前抚摸着女儿的头,无奈地说:“闺女,爹……对不住你”
翠萍用手捧起父亲的手,扬起脸,强笑着说:“爹,没啥;我……我真的……愿意呀!”
高万祥一把搂过女儿,不禁老泪纵横。堂堂的一代武林大侠,居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人家做妾,而且,他有生之年还要隐姓埋名,背井离乡,让他怎么能不感到耻辱呢?高万祥发誓:一定要手刃仇人,报这血海深仇!
这一夜,父女俩各怀心事,谁也没睡安稳。
再说郝玉川。
因为娶的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通臂王高万祥的女儿,所以,他不敢有半点马虎。第二天,他就托出了警察署长马剑飞,带着账房先生老周,提上礼物,到山西会馆找高老爷子正式提亲。而后,他又亲自上门,送来了彩礼,在沿河镇,这叫“下定”。并在沿河镇最有名的饭店——晓月楼大摆宴席,遍请各界名流,算是正式和翠萍姑娘定了亲。又找来算命先生,挑选出了迎娶的日子。巧了!算命先生推算出的迎娶翠萍的日子,也是阴历的八月初八。
消息一传开,整个儿沿河镇都轰动了。宛平县县长、国立扶轮中学的校长、铁路工厂的大总管,奉军、阎军驻京办事处的长官都送来了贺礼。铁路工厂少林会的会头出面,联络了沿河镇各“社火班子”的头儿,大伙儿商定:要把每年在“四月庙”上表演的全套社火亮出来,为郝大夫婚事好好热闹一番。沿河镇商会还凑钱请了个戏班子,准备为郝家的喜事唱三天大戏。就连沿河镇叫花子头儿“杜四儿”,也向手下人发出了狠话:郝大夫办喜事儿时,谁也不许上门去“起腻捣乱”!
这天,工匠们正忙着在寿仙堂院子里搭棚。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管家老周忙着接待着。
铁路工厂保定帮的工头李四儿走了进来,他先冲老周一拱手,笑着说:“周大哥,听说郝大夫要……办喜事儿?女方还是山西大侠、通背王高万祥的独生女儿?恭喜恭喜啊!”
老周忙着还礼,满脸堆笑地连声说道:“李头儿,同喜同喜!”
李四儿接着说:“周大哥,郝大夫这回办喜事儿,我让徒弟们把全套的‘社火’都预备下了。到了正日子,我保证让它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
老周沉吟了一会儿,为难地说:“李头儿,这事儿…我还真不敢应你。”
李四儿把眼一瞪,不快地说:“周大哥,打我脸是吧?平常日子郝大夫没少给我的徒弟们治伤看病,哪回也没要钱。如今郝大夫办喜事儿,我怎么能不‘意思意思’呢?放心,我们一个大子儿也不要。每年正月里我们保定帮的‘玩艺儿’您都瞧见了吧?耍狮子、踩高跷、少林棍、霸王鞭,那可都是绝活儿!除了郝大夫,别人家办事儿,花多少钱我可都不伺候。怎么着?我这张热脸贴到冷屁股上了?周大哥,我没得罪您吧?”
老周忙说:“李头儿,您误会了;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是郝大夫发了话,他早就料定了您得来,就提前留下了话儿,不让我应下您这挡子事儿呀!这么着吧,郝大夫就在后院儿,您自己跟他说去吧!”
李四儿把脖子一梗,红着脸说道:“你当我不敢说?我就不信郝大夫能不给我这个面子。”说罢,李四儿气呼呼地朝后院儿走去。
寿仙堂后院正房客厅里,郝大夫坐在太师椅上,正和沧州帮的工头徐天亮说话。李四儿走了进来,冲郝大夫一抱拳,大声说:“郝大夫,我这儿给您道喜啦!”
郝大夫忙站起身来,连连还礼,笑着说:“同喜同喜呀!李头儿,快坐。”
李四儿斜眼看了看坐在另一侧的沧州工头儿徐天亮,板着脸坐了下来。
郝大夫看了看二位,说道:“二位,你们沧州帮和保定帮的人说起来还是河北同乡,有啥深仇大恨?怎么就不能和解了呢?”
徐天亮说:“郝大夫,这是两码事儿。听说您要办喜事儿,我们想给您出把子力,把过年时闹社火的玩艺儿全拿出来。您为什么就不给我这个面子呢?”
郝大夫说:“我办喜事儿图个吉利,我可不想让你们两拨人在我家门口再打起来。你要想让我应下你,你必须答应和李四儿和解。”
徐天亮说:“郝大夫,不是我驳您的面子,实在是……我们两拨儿人结的仇太深了。自打我带着我的徒弟进了铁路工厂后,就没断了和保定帮的人打架……”
郝大夫生气地说:“亏你还好意思说,每年我都得给你们的徒弟们没完没了地治伤,你说我冤不冤?徐老弟,你总得替你的徒弟们想想吧?再这么折腾下去,啥时是个头儿呢?不如你给我个面子,你们……”
徐天亮站起身来,冲着郝大夫一抱拳,扳着脸说:“郝大夫,告辞!”
郝大夫一把扯住徐天亮,扳着脸说:“姓徐的,打我脸是吧?你今儿个要是敢从这儿走出去,今后永远别再登我的门!”说着话,他一把将徐天亮推在椅子上,忙又转脸笑着对李四儿说:“四哥,喝茶呀!”郝大夫一边给二人倒茶,一边说道:“二位都是我郝某的朋友,希望能赏我个脸,答应我一件事儿。”
李四儿点了下头,说道:“郝大夫,您是我们保定帮的大恩人,平常经常给我的徒弟们治伤瞧病,而且分文不取。您的话我敢不听吗?”
郝大夫说道:“好,够朋友;你们俩能坐到一块儿,真不易呀!我干脆挑明了说,你们看在我给你们的徒弟们长年免费瞧病的份儿上,就和解了吧!二位要是听我的话,郝某感激不尽,接下来咱们什么事儿都好说。二位要是不听我的话,不赏我这个面子;咱们从今往后谁也不认得谁。门在后边,二位请便!”
李四儿脸上的肌肉颤抖着,仔细咂摸着郝大夫的话,终于笑了出来。他一拍大腿,大声说:“全冲郝大夫,今天这口气……我他妈咽下去啦!”他站起身来,冲对面的徐天亮一抱拳,豪爽地大声说:“徐师父,徐老弟——;李四儿这儿……给您作揖啦!”
徐天亮先是一愣,随后慌忙站起身来,冲李四儿连连拱手,强笑着说道:“李…李师父,四…四爷……”
李四儿跨上一步,连连摆手,大声说:“别这么叫,您要瞧得起我,叫我一声‘四哥’就行了。谁让我比你大几岁呢?”
徐天亮上前握住李四儿的手,笑着说:“四哥,兄弟我过去……多有冒犯,谁让我是兄弟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饶了兄弟吧……”
李四儿抢着说:“徐老弟,你可别这么说;过去都是四哥我不够意思,心眼儿太小容不得人。我…我对不住你呀……”说来也真奇怪,说到激动之处,李四儿的嗓音哽咽了,眼圈儿也红了,眼泪终于淌了出来。他还真的动了感情啦!
郝大夫上前搂住二人的肩膀,用力拍打着,哈哈一笑说道:“满天的乌云风吹散,看你们哥儿俩和解了,我心里痛快!不过…我得问问你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待会儿出了门还算数不?”
徐天亮抢着说:“郝大夫,往后四哥就是当街打我,我都不还手。我说到做到!”
李四儿说道:“谁有那么大胆子?往后谁再欺负我徐老弟,我李四儿绝不答应!”
郝大夫把二位重新让到椅子上,笑着说:“二位,沧州和保定可都是出好汉的地方;我得我问你们,论起功夫来,在江湖上是沧州人厉害、还是保定人厉害呀?”
李四儿咽了口唾液,极不情愿地说:“天下功夫属沧州哇!武林中谁不知道?镖局的镖师押镖打沧州地面儿上过,一不许亮镖旗,二不许喊镖号,这是多少年的江湖规矩。如若不然,非得栽在沧州地面儿上不可呀!”
徐天亮连连摆手,笑着说道:“要论拳脚功夫,咱直隶地面儿上那得首推保定府。远的不说,自清朝以来。保定府一直是住兵的地方,日子长了,军营里的士兵就把功夫传到了民间。特别是善扑营中的摔跤好手,被军队裁撤下来以后流落民间,之后差不多都成了武馆的教师爷。所以,保定地面儿上的跤手十分厉害。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是:‘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咱就说四哥的侄子小白龙儿李谦吧,来沿河镇半年多了,人家愣是从未失过手。佩服!”
郝大夫眉飞色舞地说道:“二位,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也就放心了。后天是我的好日子,你们两拨人都来,越热闹越好哇!可有一样,你们得安排好了,别在大街上再争起来。家有百口,主事一人;你们俩只能有一人全面调度,省得出乱子。”
徐天亮大声说:“我听四哥的,四哥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
郝大夫说:“你的徒弟们听招呼吗?”
徐天亮说:“放心,回去我就找他们把话挑明。我还打算往后也让我的徒弟们去龙王庙跟小白龙儿学摔跤哩。”
三人大笑起来。
康家的丧事还在进行着,郝家的喜事儿也在紧张地筹办着。转眼间,可就到了八月初八。这一天,永定真可谓“万人空巷”,康、田两家“办事儿”的场面惊动了沿河镇,直到五、六十年之后,沿河镇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向儿孙们叙说着当时的热闹场面。
天刚亮,沿河镇各路“社火头儿”就带人来到了寿仙堂前,吹吹打打地表演开了。踩高跷的,一个个都扮上了戏装,打扮成了戏剧舞台上的人物,踩在一人多高的“跷腿子”上,卖力气的表演起来。沿河镇上这伙踩高跷的,都是铁路工厂的工人。他们分别来自河北省的沧州、保定,全是有名的武术之乡。平时,这两拨儿人谁也不服谁,甚至还不断地闹点儿小磨擦。然而,他们都欠郝大夫的人情,更敬重郝大夫的人品,所以,今天都专门赶来,为郝大夫的婚事捧场。
这伙“闹社火”的小伙子们,人人都有绝活。那表演跑驴的,其实是个壮年汉子,但却描眉画眼儿地打扮成了俊俏的小媳妇儿模样,架着“驴形”,做出各种奔跑、上坡、下岗、尥蹶子的动作,表演得十分逼真。另一个小伙子扮成丈夫的模样,围着“驴”不时作出各种惊险、滑稽的动作;引逗得观众不时发出阵阵的笑声。那“跑旱船”的,取材于京剧舞台上的折子戏《秋江》里的情节,表演者是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他俩此时的身份分别是老艄公和小尼姑陈妙常;俩人彼此不住地插科打诨,逗得人们不时哈哈大笑。
最有气势的,当属铁路工厂沧州帮少林会表演的“跟斗会”。20来个壮小伙子,都是“短打扮”,一身黑色的练功服,腰扎软带,脚蹬软底儿快靴。他们排成队,在空场上翻出各种漂亮的“跟斗”;像什么虎跳、小翻儿、大车轮都不新鲜了,有人竟然翻出了奇、险、绝、俏的“三百六”。让人看了忍不住就会扯开嗓子大声叫“好儿”。迎亲的时辰还没到,寿仙堂门前的表演已经高潮迭起,观众们的呐喊声已经震天动地了。
寿仙堂管家老周忙招呼着伙计在门口儿支了桌子,沏了大碗儿茶,放上了成条儿的香烟。他不停地向人们作揖致谢,连道:“辛苦”。老周和伙计们心里像喝了密似的,舒坦!除了郝大夫,沿河镇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要知道,除了一年一度的“火神庙会”,谁也无法把这些人聚拢到一块儿。他们之间原本就矛盾不断,谁也不服谁,凑到一块儿时,哪回也得为争风头动手打架。而今天为了给郝大夫捧场,沧州帮和保定帮的人都主动来了,而且两拨儿人拧成了一股劲儿,齐心协力地为大家奉献出精彩绝伦的表演。作为寿仙堂的人,怎么能不得意呢?老周抖擞精神,满脸堆笑地把桌子上的香烟拆开来,热情地给人们递上去。另一个伙计,赶紧跟在后头给大伙儿点烟。
吉时一到,大伙儿忙又演练起来。保定帮的一对威武的“狮子”,在一个武士模样的小伙子的引领下在前头开道,后边紧跟着的就是一拨儿踩高跷的。再往后就是小车儿会、旱船、跑驴、太平鼓。表演队伍走完了之后,八个轿夫才抬出来一顶装饰艳丽的花轿。一拨儿吹鼓手围着花轿起劲儿地吹打着“百鸟朝凤”。花轿后边,就是骑一匹高头大马,十字披红的新郎官郝玉川。他满面春风地向四周的乡亲们频频拱手作揖、点头儿示意,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郝大夫今个笑容满面,乐得都合不上嘴了。高头大马的四周,便是少林会那20多个翻着跟斗的小伙子们。迎亲的队伍摆了足有一里地长,沿河镇大街完全被迎亲的仪仗占满了。
按沿河镇的习俗,迎亲的队伍是不能走“回头路”的。也就是说,抬着空轿子的迎亲队伍,在接上新娘子之后,是不能再原路返回。于是,在前边引路的一对狮子,引导着迎亲的队伍在离开寿仙堂大门口儿之后,提前就进了小胡同。为的就是等接上新娘之后,就能名正言顺地从沿河镇繁华热闹的主街道上返回寿仙堂。郝玉川骑在马上,望着前边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和街道两旁围观的人群,他长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场面也算对得起高家父女了……”
就在郝家的迎亲队伍上路的同时,康家“出殡”的队伍也出发了。
康老太爷早就订好了出大殡的吉日,又根据吉日,才定出了此前一系列的举丧仪程。折腾一个来月了,就为了今儿个好好儿地当众显摆一番哪!康家的大门口前,搭起了用松枝扎成的“牌坊”。牌坊两侧高挑着一副白纸黑字的对联儿,上联写:“驾鹤西游、音容笑貌留千古”。下联写:“德隆望重,祖宗福命是神仙”。吉时一到,先由他的长子康万金当街摔碎了一个瓦盆儿,随着“叭”的一声响,康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全都咧开嘴同时放声大哭起来。吹鼓手立时吹奏起了悲悲切切的“哭皇天”,“杠头儿”用香尺敲出了节奏,指挥着杠夫们缓缓抬起带棺罩的棺材,送葬的队伍便缓缓起动了。
走在最前边的,是一群打着白幡儿的人们。遮天蔽日的白幡迎风飘动,刷刷作响,很有气势。纸幡阵后边,是一群请来的吹鼓手。吹鼓手后边,是由女眷组成的方阵。她们每人手上都擎着一把纸糊的白伞,看上去也很齐整。“伞阵”后边,先是喇嘛,后是和尚,再是尼姑,他们敲打着手上的法器,嘴里咿哩哇啦地念着经,缓缓而行。出家人之后,便是一大群手擎各种“纸烧活”的半大孩子。这些孩子全是主家花钱雇来的,他们只觉得好玩儿,脸上根本没什么悲伤的神态。
身穿重孝,扛着“招魂幡”的大孝子康万金,在俩人的搀扶下,咧着嘴干嚎着:“爹呀,你老人家怎么说死就死啦……”
康万金身后,是康和轩另外几个儿子,他们也都一脸木然,隔一会儿来一嗓子:“爹呀——”
包括老大康万金在内,康和轩的这几个儿子谁也哭不出来。老爷子明明还活着,却让他们满大街的哭爹,这不是拿他们当猴儿耍吗?为了让老爷子高兴,家里已经瞎折腾一个月了。买卖不能做,什么事儿也不能干,每天就是跪在那口空棺材前哭爹,还要见人就下跪,满街筒子去磕“孝子头”;这算什么?老爷子这么做到底图个什么?有钱怎么花不成,何苦要出殡玩儿呢?弄出这种“洋相”来,让儿孙们往后怎么见人呢?
康和轩和儿子们之间的矛盾,其实还远不止表面上这些。
从内心来说,儿子们其实没有一个不恨他的。若不是受传统的“愚孝”观念的束缚,儿子们甚至可能把他杀了。他做事儿实在太过分啦!康和轩好色成癖,竟然到了灭绝人伦的地步。每个儿子娶亲后,都得让康和轩这老东西先睡头一晚上。那年月男子都娶亲早,有钱人家尤其这样。所以,康家小哥儿几个都是十四五岁就成了亲。早年间兴娶“大媳妇”,为的是媳妇过门儿后能让着小丈夫,还能帮着家里干活。所以,康家的几房儿媳妇过门儿时,都十七八岁了。谁会想到,待完成了一系列娶亲的仪式之后,康和轩这个老东西居然抢着替儿子入了洞房,先于儿子尝了鲜儿……
对康和轩这种禽兽行径,自小就被他打怕了、打服了的儿子们,竟然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的。他们甚至以为:普天下当儿子的,都得把婚后的“初夜权”让给自己的老子。新媳妇被老公公强奸了之后,自然更不好声张。但儿子们大了之后,谁不懂事儿?他们虽不敢与老父亲公开理论,但内心却恨透了这禽兽不如的爹。那年月讲究愚忠、愚孝,讲究“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是为不孝。”历来的衙门口儿,只惩办那些“忤逆不孝”的儿孙,从来没见有哪个强奸了儿媳妇的公公被官府惩治。何况“家丑不可外扬”,除了对老爹怒目而视,儿子、儿媳妇也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
在康和轩的四个儿子中,只有老四康万刚,对老父亲的“扒灰”行径进行了反抗。康万刚十六岁那年,正在扶轮中学上学,家里就为他娶了亲。当天晚上,当康万刚看见老父亲进了原本属于他的“洞房”时,便一跺脚,坐上火车离家出走了;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嫁过来当天就被老公公强奸了,丈夫又扔下她跑得没了踪影;康万刚的小媳妇又羞又恨,第二天就上吊死了。康家有钱,除了给那小媳妇的娘家一大笔钱,又在警察局、宛平县衙门里上、下打点,之后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康家父子之间有此“过节”,哪个儿子能不恨禽兽不如的康和轩呢?这回康和轩竟要儿子们给他办一回“活出殡”,儿子们对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顺着沿河镇大街缓缓而行。按沿河镇的规矩,与死者生前交好的,还得在当街设摆香案进行“路祭”。何况,康家众多店铺里的伙计、管事儿的,都是受雇于康家,谁敢不趁机“表现”一番?瞧见没有,老当家的可就在后边儿滑杆儿上坐着哩,惹恼了他,明天就得卷铺盖滚蛋!于是,康家店铺的伙计们,不等送殡的队伍来到跟前,早早就在当街支好了供桌,预备好了供品、烧纸。待送殡的队伍一到跟前,伙计们忙伏在供桌前,点燃了“烧纸”,边磕头便大声念叨着老掌柜的“生前”的恩德。自然,甭管真的假的,还得哭上那么几声。就连“红房子妓院”的妓女们,也在老鸨的带领下,哭哭啼啼在当街对“老当家的”进行了路祭。于是,这送殡的队伍便走走停停,缓慢地由南向北行进着。
坐在滑杆儿上的康和轩当然不嫌慢。他花钱这么一通折腾图什么?不就是为了当众摆谱儿,往自己脸上贴金吗?不就是为了在人前显贵,在沿河镇老少爷们儿面前露脸、拔份吗?既然花了钱,摆了这么大的排场,干嘛不慢慢儿地享受呢?何况他坐在滑杆儿上,上边儿还有遮阳的篷布,又不累又不热,急什么?康和轩满脸堆笑,还不时在滑竿儿上向路祭他的人们拱手致意呢。
然而,抬杠的杠夫们可累坏了。按规矩,这棺材一抬起来之后,沿途是不能落地的,必须一口气抬到墓地,入土为安。康和轩的这口棺材虽说是空的,但厚重的柏木棺材,加上棺架、棺罩,那分量可不轻。两根两丈长的圆木棒在了一起,就是“棺架”。圆木上又分成若干个“小杠”,小杠上又分成了“小抬”,总共用了四十八个杠夫,才把这口棺材抬了起来。为了能让棺材沿途不落地,就得提前预备替换的杠夫,这送殡的人无形中又多了几十口子。本来不算窄的沿河镇大街,被送殡的队伍塞了个严严实实,对面要是来了车辆行人,那就只有钻胡同绕行了。对于给别人造成的不便,康和轩并不觉得愧疚,他认准了一条死理儿:“死者为大”,行人、车辆都得给送葬的队伍让道儿;这是沿河镇人共同认可的老规矩呀!
再说郝家迎亲的队伍。
在一对儿活蹦乱跳的“狮子”的引领下,娶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来到了山西会馆门前。各路助兴的“社火班子”便在山西会馆门前拉开了架式,卖力地表演起来。民间耍社火,本来就是争风头的事。各档花会之间,历来是谁也不服谁。今天虽说都是来给郝玉川捧场、帮忙的,但也是各不相让,逗气儿、较劲的事儿自然免不了。上场表演的都十分卖力,为的是要赢得人们的喝彩声。表演的人总嫌时间短,逮住机会就折腾个没完没了。而在一旁等待上场的人自然不免心急,双方免不了口舌之争。寿仙堂账房先生老周两边维持着,一个劲儿地给双方作揖说好话,又加上李四儿和徐天亮两个“工头儿”帮着维持着,现场总算没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儿来。
围观的人们不时发出阵阵喝彩声,鼓掌声响成了一片。然而,骑在马上的郝玉川可是苦不堪言,太阳的暴晒,让他和跨下的马都大汗淋淋,出汗太多,他觉得嗓子眼儿又粘又苦。然而,他却不能催促表演的人们,人家是来给他捧场、助兴的,除了感谢的话,他还能说什么呢?心里着急上火,但脸上还得微笑着。渐渐地,郝玉川脸上的笑容可就成了苦笑了……
谢天谢地,大伙儿的表演总算在老周的央求下结束了。郝大夫这才下了马,在众人的簇拥指点下,进了山西会馆的大门,来到了高家父女暂住的房中,先给老岳父高万祥行了大礼,然后才把打扮得花枝招展,且蒙上了红盖头的新娘子翠萍姑娘接出来,扶上了花轿。鼓乐声又起,娶亲的队伍沿着沿河镇正街,自北向南奔寿仙堂药铺走去。
沿河镇素有拦花轿的习俗,但凡沿河镇的姑娘出嫁,婆家的花轿休想顺顺当当地出沿河镇。一般来说,女方家里的人缘儿越好,社会地位越高;拦花轿的人就越多。人们认为:沿河镇的姑娘,倘若让外人轻易地娶走了,日后到婆家肯定会遭人轻贱。作为娘家人,大伙儿怎么也得帮着新娘子长长威风啊!得让婆家知道:沿河镇的“姑奶奶”可不是好欺负的!
另一层意思是:拦花轿的人多,说明这姑娘可人疼,招人喜欢,大伙儿舍不得她嫁出去。拦花轿的人,实际上是给嫁姑娘的本家助威、长脸,说明这家子人有人缘儿。拦花轿的人越多,“本主儿”越有面子。
拦花轿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无论是谁,只要搬个凳子往当街一坐,迎亲的队伍就得停下来。这时,新郎必得上前打恭作揖说好话,还得主动给拦花轿者献烟、敬糖,直到把人家哄得高兴了,这才把凳子搬开,放娶亲的队伍前行。
虽然翠萍姑娘不是沿河镇的“姑奶奶”,但人们都敬仰郝大夫的人品,所以,花轿刚走了不到一百米,就被人拦住了。老周忙上前笑着敬烟让糖,然而,拦花轿者不依不饶,非得让各路“社火班子”表演一番不可。还没等老周表态,社火班子的人便主动地在当街上拉开了场子,又闹开了……
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娶亲的花轿,自打一出娘家门,不到婆家是不准落地的。据说,花轿倘若在中途落地,两口子就过不到头。队伍被人拦住了,抬花轿的八个人见无法前进,就一打招呼,抬着花轿,原地“悠”开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轿夫们把花轿“悠”起来后,轿内的新娘子便会吓得大声喊叫,连连向轿夫们告饶。而轿夫们根本不理会,继续折腾着轿内的新娘子。直到新郎心疼了,上前来央告,而轿夫们便会趁机向新郎提出要求——“加钱”。新郎答应下来,轿夫们这才停止了善意的恶作剧。自然,轿夫们并不真的是为了加钱,而新郎官儿这会儿所说的话,通常事后也并不兑现。人们只不过是借办喜事儿凑热闹,相互开玩笑罢了。
谁知,今天的事儿邪门儿了;轿夫们把花轿悠成了“秋千”,轿内的翠萍姑娘却不吭一声。轿夫们找不着开玩笑的缘由,便大声逗开了:“我说,咱们今天抬的这位新娘子可够沉啊!”
“可不,我说哥儿几个,咱不会是抬错了人,连丈母娘、小姨子一块儿都抬来了吧?”
四周看热闹的人“轰”的大笑起来,郝大夫忙下了马,走到花轿前一拱手,满脸堆笑地说:“几位辛苦,回头咱们加钱、加钱!”
轿夫把嘴一撇,说道:“加多少钱哪?仨瓜俩枣儿就把我们哥儿几个打发了可不行。”
“每人加一块现大洋!”郝大夫笑眯眯地说。
“一块不行,每人五块!”轿夫头儿故意提高了嗓音大声说道。郝大夫忙随口答道:“一定、一定啊!”
谢天谢地,迎亲的队伍总算又开始走动了,轿夫们才停止了调侃,抬着轿子继续朝前走去……
娶亲的队伍从寿仙堂出发时,是自南向北行进,才到达高家父女暂住的山西会馆的。接了新娘之后,队伍就改由自北向南行进了。也就是说,郝家的迎亲队伍,和康家的送殡队伍,正好走了个“脸儿对脸儿”。两拨儿队伍终于在警察署门前僵持住了。
郝家这边,吹鼓手们不管不顾,又趁机吹奏起来。而康家那边,雇来的吹鼓手们也不甘寂寞,他们索性冲到了队伍最前边,和郝家雇来的吹鼓手对上了阵。在沿河镇,一旦两拨儿吹鼓手对上了阵,讲究不把对方“叫”趴下不罢休。什么才算叫“叫趴下”?那就是自己这一方稳住阵脚,使劲地吹奏,一曲连一曲地吹奏下去;直到把对方的节奏搅和乱了,让对方不由自主地跟着你这一方吹奏的曲子走了,这才算罢休。胜了的一方,当众露了脸,日后人家来请的机会也多。而败了的一方,往后应酬的价钱就会低了许多了。事关“饭碗子”,吹鼓手们谁能不卖力呢?
然而,办事儿的主家是耽误不起的。那年月干什么都讲究个“时辰”,过了“吉时”可就不吉利了。比如郝家此次娶亲,按沿河镇的习俗,新娘子必须在中午之前赶到婆家,才算吉利。而且,郝家还请来了厨子,预备了家宴,完成了这一整套娶亲的仪式之后,还得招待客人喝喜酒呢,真的耽误不起呀!
沿河镇人信奉“死者为大”,一般娶亲的和送殡的队伍倘若狭路相逢时,都是娶亲的给送殡的让路。本来,这“乡规民约”大伙儿都是认可的。按说郝家的娶亲队伍,应当给康家送殡的队伍让路。其实也不算什么,娶亲的队伍只要往大街的道路一侧一让,送殡的队伍将就这也就能过去了。可康家的送殡队伍并不是真送的“死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为大”;郝家娶亲的队伍当然不肯为瞎胡闹的“活出殡”让路了。又何况,康家在沿河镇根本就没人缘儿,老混蛋康和轩替儿子跟儿媳妇“睡头一晚上”的丑闻人人尽知。四儿子就为“这个”离家出走了,新媳妇第二天就被逼得上了吊;康和轩缺了大德啦!有此丑闻,还会指望别人会给他“让道儿”吗?根本就用不着主家发话,郝家娶亲队伍里的人就和康家送殡的人当街“杠”上了!
郝玉川用手抹了把汗,打发人把老周叫到了跟前,无奈地吩咐道:“周大哥,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啦!告诉前边领道儿的,咱钻小胡同过去,给出殡的让道儿!”
老周为难地苦笑了一声,说道:“郝大夫,不行啊!大伙儿较上劲了,咱们的人说什么也不肯让。”
“大哥,你胡涂啦?死者为大嘛!”
“郝大夫,这道理谁不懂?对方要真是死人,那还用咱交待、吩咐吗?”
郝玉川无奈地笑了。关于康和轩“活出殡”的闹剧,他自然也听说了。如此说来,给对方让路的理由,似乎……就不那么充足了。他想了想,便大度地说:“咱跟他计较什么?告诉弟兄们,办咱的事儿要紧,别把吉时耽误了。咱哪,还是钻小胡同。”
“不行!”老周把脖子一梗,执拗地说:“郝大夫,咱接亲时可是钻小胡同过去的,再走小胡同回去,那不是走‘回头路’吗?不吉利呀!”
“那……”郝大夫又抹了把汗,焦急地说:“咱就这么耗着?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老周叹了口气,小声说:“好,我跟大伙儿再商量商量吧!”说罢,又转身朝前挤去。
这时,两拨儿吹鼓手已经放下了乐器,对骂上了。康家雇来的吹鼓手们虽然不能为康家的“活出殡”行径辩解,可同行是冤家,既然撞上了,当然不能让啦!这回要是当街跟同行儿的人认了怂,往后在这行儿里还怎么混?为了自己的“饭碗子”,也得跟对方死磕!
郝家雇的吹鼓手更是理直气壮,所谓“得理不饶人”,当然得跟对方的同行们较劲啦!更让他们底气足的是:他们受雇于寿仙堂的郝大夫,哪里是臭名昭著、扒灰成性的康和轩能比得了的?就冲“这个”,他们就自觉高出对方一大截儿!先是吹鼓手们骂骂咧咧、推推搡搡,接着玩社火的人也上前助阵,眼见得康家这边儿的势头很快就被压下去了。老周上前来劝,可发起火来的人们,已经不听他指挥了。踩高跷的人们站的高,嗓门儿也特别大,指着康家送殡的队伍就开了荤:
“给活人出殡,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有钱是啵?有钱去买‘前门楼子’呀!”
“牛X什么呀?连他妈自个儿姓什么都不知道,太监从外边儿抱来的儿子,指不定谁家的野种呢!说不定还是头些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做’出来的哩……”
污言秽语,夹枪带棒,句句捅对方的心窝子。很快就引起了旁边儿围观的人们的哄堂大笑,这笑声无异于给骂人的这一方站脚助威,使得娶亲的这一方的气势彻底压倒了对手。康家的出身让人看不起,康和轩“扒灰”的丑闻更令人发指,平常人缘儿就差,“活出殡”的闹剧更不得人心。一会儿的功夫,两拨儿吹鼓手之间的争吵、对骂终于演变成了对康和轩的指责、嘲笑。先是念经的和尚、尼姑索性闪到了一边,紧跟着康家花钱雇来举“烧活”的孩子们也都散开了。女眷们听不惯那些污言秽语,尤其是康家的几房儿媳妇,一听有人提康和轩“扒灰”的事儿,更是羞愧难当,也都扭脸躲开了。于是,康家的几个儿子,便成了康家出殡方阵中的“排头兵”。康家的弟兄们把目光都转向了大哥康万金。而一向懦弱的康万金此刻却面如死灰,脸上毫无表情,根本没主意了。
首先,康万金心里承认:老爹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根本就不占理。因此,他根本没有勇气与对方争执。人家说得对呀!“死者为大”不假,可老爹他并没有死,那么他跟谁“充大”?凭什么要求人家正经的娶亲队伍给一场“瞎胡闹”让路呢?他从心里已经站到了对手的立场上,不由得方寸大乱了……
然而,老大康万金却不敢像其他两姓旁人那样,闪到一旁去看热闹。他是家里的长子,从小让老爹打服了、打怕了、打傻了;老爹让他去死,他也不敢说半个“不”字。没有老爹的命令,他哪敢躲呢?康万金闭上了眼睛,呆呆地站在棺材前边,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不动窝儿,其他的兄弟们自然也不敢动……
闹社火的这些人,不是郝家雇来的,而是主动来给郝大夫帮忙的。大伙儿都不愿耽误了“吉时”,便行动起来,对康家送殡的方阵进行着更猛烈的冲击。踩高跷的踩着鼓点儿,在康家兄弟面前大幅度地跳跃着。“跟斗会”的这帮小伙子,也翻着跟斗,几乎撞上了康家兄弟。康万金终于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歪,便昏了过去。他的兄弟们忙抱起了他,趁机闪到了一边。这时,郝家的人直接面对那口棺材了。不知是谁带的头,杠夫们把棺材放在地上,一下子也散开了……
在双方僵持住了的时候,康和轩还以为是又有人路祭他了,所以并没在意。直到棺材落了地,康和轩才急了。他指着杠夫们破口大骂道:“我操你们姥姥的,棺材不能落地,知道不?有他妈你们这么办事儿的吗?我不给钱哪!”
然而,没人理睬康和轩的喝骂,杠夫们撂下棺材,已经全跑了。康和轩下了滑杆儿,挤到了棺材前边。当他看清了前边正是郝家的娶亲队伍时,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子事儿。康和轩气得五官都挪了位,浑身颤抖着,指着郝家娶亲的队伍一蹦老高地破口大骂起来:“姓郝的,有那份儿‘能耐’吗?也他妈张罗着娶小媳妇?呸——!你他妈言语一声,康大爷我辛苦辛苦,怎么也帮你‘弄’出个三男两女的来,好歹往后也有人替你收尸呀!明明是头‘骡子’,也他妈张罗着学驴叫唤;你他妈叫也是白叫……”
人常说,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康和轩骂出的话实在太损了,等于是用刀子捅郝大夫的心窝子呀!因为夫人不生育,郝大夫非常痛苦,全沿河镇的人,从没有人拿郝大夫“这档子事儿”来谈论。何况,坚持不给康家送殡的队伍让路,并不是郝大夫本人的意思,假如康和轩跟郝大夫好好商量,郝大夫肯定会给他让路的。但康和轩此话一出,这事儿可就绝对没商量了。铁路工厂少林会这帮小伙子谁吃这套?康和轩的一张嘴又怎么能骂得过人家几十张嘴?踩高跷的那伙人把康和轩围在中间,朝他又啐又骂。康和轩又气又急,便拿出他的泼皮无赖劲头,冲对方一头撞了过去,嘴里高吼道:“康大爷我不活喽——”就这一下子,康和轩当时就倒地中了风,口眼歪斜、口吐白沫,登时不省人事了。
人们以为康和轩是在耍无赖,便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康和轩抬了起来,抬到了大街旁边。众人又将那口空棺材也抬到了旁边,娶亲的队伍像潮水般地朝前涌去,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朝寿仙堂方向走去。
一点儿没耽搁,中午之前,翠萍姑娘乘坐的花轿顺顺当当地抬进了郝家。两口子完成了拜天地、迈马鞍等一系列仪式之后,郝家的喜宴便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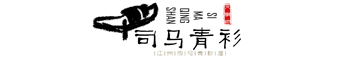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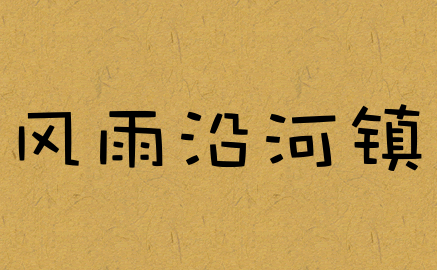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