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从不说她是聋子。因为我和奶奶之间交流,根本不用说话,我只摆摆口型,我奶奶就“听”懂了。
我奶奶去世的时候84岁,一辈子五儿五女,到老来给她养老送终的,却只有我的两位伯父。所以,我奶奶总是不停地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忧伤。
关于我奶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羊皮袄和那把包了布边的芭蕉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乡下演电影都是在户外,而且都是在东庄上或者西庄上。农村里,春夏秋三季都很忙。冬天,人闲了,夜也长了,这时候才演电影。
无论在哪儿演电影,我都很少去看。因为每次去看电影,奶奶必然让我穿上她的羊皮袄。那袄死沉死沉的,穿到我身上像羊皮大衣。小小的我驮着这么重的袄,跑到演电影的地方,每次都累得精疲力竭,热得满头大汗。看完电影,再驮着那大皮袄回家,感觉像小蜗牛背了一个重重的壳……
我到现在都怕冷,这也要归功于我奶奶。她总是觉得我冷,一到冬天恨不能把所有能套到我身上的衣服,都给我套上。
记得那一年,我都五年级了。夜里下大雪,白天上学去,奶奶非要在我的棉衣之外,再套上她的棉坎肩。那坎肩黑色,我穿到身上,下摆差不多拖到脚后跟,奶奶非要说这样才暖和。我拗不过奶奶,只好把坎肩穿上,刚出了家门,就脱下来抱在怀里。奶奶远远地看着,也不生气:不穿就抱着吧,抱着也暖和!因而,小伙伴们都冻手冻脚,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
夏天的夜晚,铺了苇席在院子里乘凉。奶奶摇着芭蕉扇,我数星星。一会儿从东边数,一会儿从西边数,一会儿又从最亮的开始数。数累了就让奶奶唱儿歌。我奶奶不会讲故事,只会哼几句儿歌:
小红鞋,金线锁
出门碰见娘家哥……
唱到这儿,奶奶突然就不唱了,她摇摇手中的芭蕉扇,要我唱一个。于是,我就唱起来:
小大姐,溜坑沿
洗白手,插花鞋
插了花鞋搁哪儿
搁到爹爹床头上
爹爹看了心欢喜
婆婆看了就要娶
娶到哪儿,
娶到东北大庄上
又有车又有马
还有小孩吹喇叭……
我奶奶是听不到的,我每次唱完,就把两只手卷成小喇叭,奶奶一看就知道我唱了什么。
凉快透了,进屋睡觉。我睡的时候,奶奶给我摇扇子,醒来的时候,那把包了布边的芭蕉扇,和我并排躺着,我奶奶已经起来操劳去了。
我奶奶的耳朵,是日本人的枪声震聋的。日本人进村了,我大伯逃走了,我奶奶急着要出去找,日本人不让,就在她身边开枪,因此震破了耳膜。后来,日本投降的时候,又在中国投下了大量的细菌弹,我们村有很多女孩子都死于那一场霍*乱。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姑姑,她们当时都已说妥了婆家。
1972年,中日两国第一次建交,当时我才四五岁,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爷爷用他的拐棍,狠狠地戳着地面,愤然说:中国人啥时候都不能和日本人好。他担心中国人会吃日本人的亏,就像担心我会受婆婆的气一样。
我爷爷听小曲子戏《王三姐打棒槌》,回家看到我就掉眼泪,他担心我在婆家受了气,没有嫂子去帮我出气。我奶奶唱儿歌,唱到“出门碰到娘家哥”,突然就不唱了,也是这样的情怀。
其实,我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我的童年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因为跟着爷爷奶奶,我小时候不用看弟弟妹妹,长大一点不用纺棉织布做鞋子。我有的是时间去唱儿歌,去猜谜语,去看云彩,去听别人讲故事。
但是,我奶奶认定我是苦命的人,每天为我的未来处心积虑。不仅如此,她连我爷爷也不相信,背着我爷爷,偷偷给我攒下三十块钱。她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为了保护我,她依然选择不顾一切。她恨不得我一天就长大嫁人,然后,她才可以心无挂碍地活着或者死去。
我奶奶在的时候,我没感觉到特别温暖。我奶奶去世了,我才感觉到,人间如此荒凉……
事实上呢?我没有受婆婆的气,我也没给婆婆气受,中国人也没有再吃日本人的亏。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患难才能见真情。2020年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疫情,让中国和日本,再次站到一起,在抗击新冠疫情的道路上,互帮互助,互通有无。
写到这儿,忽然想到华为、想到任正非。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对女儿的不公平待遇,任正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
“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
这才是人类的大格局,也是人类的最终走向!
本来想写写我的奶奶,怎么写到这儿来了呢?
愿人类熄灭所有的战火和仇恨,走上真正的和平!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她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者:宗风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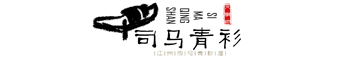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