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双栖?那不就是阴阳两面人吗?我说。
不错。张老顺说,不过这里所说的阴阳两面人是实际意义上的阴阳两面人。
怎么?阴阳两面人还分实际意义和非实际意义?我听不明白。
当然要分。世人所讲的阴阳两面人多指品行不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奸诈小人。而我今天所讲的阴阳两面人,既能生活在阳世间又能穿行于阴世间,所以称为阴阳双栖。张老顺说完,又优哉游哉地装上一锅烟,若无其事地“吧嗒、吧嗒”抽起来。
我有点害怕。试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可以在阴曹地府畅行无阻,这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活人还怎敢和他打交道?我如果见到这样的人还不吓个半死!
见我的表情有些异样,张老顺忍不住笑了几声,说:这个交道嘛,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只要你心里不把他当做那种人就行。我年轻时到过鬼城丰都,人们都说丰都大街上行走的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可我在那里不感到丝毫恐怖。另外,阴阳两面人还有一个称呼叫师婆,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师婆就是巫婆,听说过。我对张老顺说,自己从小就对师婆的行为有怀疑,认为她们那种虚张声势的所谓作法,纯粹是吓唬人的,无非是骗吃骗喝骗钱财而已,一点作用都不起。
张老顺说:骗人的师婆当然有,但也有例外。比如这一集里的阴阳两栖者就不像是骗人的。当然,他去过的阴间咱也没有去过,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但我还是比较相信他的。
我突然想起,张老顺说这一集《阴阳双栖》与张根奎的儿子有关,莫非这个儿子就是有关阴阳两面人不成?
我向张老顺印证这个问题,张老顺点头称是。
我说:师婆不是女的吗?怎么一个大男人也当师婆?
张老顺说:这就是男巫,太行山区极少见到,但别处却不少,听说外国的男巫更多。
我很惊讶,张老顺一个看羊的老汉竟然知道外国有男巫。这个不假,特别是在南美洲,男巫很多。
张老顺说:在莲浦一带,男巫有个别名叫马公。人常说,物以稀为贵。正因为这里的马公特少,所以出现一个就特别引人注意,就像城市大医院里的妇产科大夫一样。
妇产科大夫?阴阳两栖的马公怎么和妇产科大夫联系在一起?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张老顺说:我是打个比方,其实马公和妇产科大夫没有必然联系。我听说妇产科大夫几乎清一色都是女的,偶尔有一个男大夫,那人品和技术一定是出类拔萃的。马公亦是这样,村里办丧事大多数是女性师婆出面。而一旦是马公出面,那就肯定是非常重要和隆重的丧事。马公的水平也较高。好,我已经交待清楚阴阳两面人,现在开始讲咱们的故事。
张根奎的儿子名叫张依柳,是妈妈柳翠所起,从字面看,显然是为了纪念她去世的父母而起的。孩子长到十来岁时,有一天,柳翠领着张依柳到邻村皇留口去赶庙会。庙会上很热闹,买东西的卖东西人来人往比肩接踵。柳翠手牵着儿子在人群里穿梭,给儿子买了几样玩具和小吃。看看天色不早,柳翠准备领着儿子回家,忽然,她觉得眼前倏然飘过一丝光亮,亮的晃眼。这时的太阳已经快要落下西山,哪来的光亮?柳翠以为自己眼花了,揉揉眼睛想仔细看一看,不料脑袋一阵眩晕差点栽倒在地。她赶紧站稳身子,用手按了按脑门。莫非是累的?是啊,在庙会上转悠了大半天,只是给儿子买了点吃物,自己却水米未进,肚里咕噜咕噜正叫的欢呢!柳翠来到一个小食摊,要了一碗馄饨,刚要吃,突然,那道亮光又出现了。柳翠顾不得吃饭了,两只眼睛紧紧盯着这道亮光。这回她看清楚了,在小吃摊前面十多丈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右侧臂弯里擓着一个白色小篮子,篮子里装满了东西,上面盖着一层雪白的抹布,像是走亲访友一样。这一点倒不奇怪,莲浦一带的人串亲戚,女的大都擓个篮子,男的则在肩头打个“捎马(褡裢)”。但让柳翠颇感奇怪的是这个老太太的装束很特殊:上身的褂子非常大,快要遮住膝盖了,裤子却很短,裤角在脚踝以上。更让柳翠惊异的是老太太的白色小篮子。这个小篮子柳翠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是柳条编织而成。柳条还是上等的好柳条,编织手艺也很高明,所以在夕阳西下时反射出耀眼的亮光来。柳翠看着看着,心头突然一阵狂跳不止,胸口也有些发憋,堵得难受,呼吸急促起来。她想,莲浦一带从来没有这种柳条篮子出现,今天这个擓柳条篮子的老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天色渐晚,老太太在前面站着,像是等什么人似的。她要等谁?这时,柳翠见老太太也向她这里张望。莫非是等我?柳条篮子只有我们柳家的族人会编,老太太莫非也是我柳家的人?小时候听父亲说,柳家人丁不旺,没有听说有这么一位族人啊!
柳翠又把目光集中到老太太的大褂上。这一看不要紧,心里又是一阵狂跳,原来大褂的下摆衣襟是用麻绳缝的。麻绳缝衣服的针脚很大,柳翠老远就看见了。这个缝法柳翠再明白不过了,太行山深处莲浦一带,只有师婆才用麻绳缝上衣的下衣襟呢!
这时,一个思维链条在柳翠的脑海里逐渐形成:这个老太太是来找自己的,这个白色小篮子等于和自己对上了暗号。可她是个师婆,找自己又是为了什么呢?哎呀不好,都说师婆是阴阳两面人,他们找上门来肯定没有好事情。难道、难道是丈夫张根奎出了什么问题?丈夫是个条匠,整天爬坡上岭割荆条,山高路险很是危险,每天出门自己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小心小心再小心。可看老太太的样子,似乎又不像是丈夫出了问题,因为老太太的脸上似乎带着笑容。莲浦一带的风俗习惯规矩极为严格:谁家办丧事,师婆要和东家同悲同哭,面带嬉笑是要挨骂甚至挨揍,是要丢饭碗的。
既然排除了丈夫张根奎出事的可能性,那家里还有谁会遭遇不测呢?柳翠又想到了自己,但随即就被排除。自己虽然嫁给张根奎后几乎成为货真价实的凡人一个,但柳仙的基因还在,关键时刻自保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只要上天的雷公电母不来找麻烦,凡间的那些道行浅显的神怪是奈何不了自己的。一家三口人她想到了两个,唯独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张依柳。在她看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少不经事与世无涉,能有什么问题呢?然而,柳翠哪里知道,师婆的出现恰恰就是为了张依柳而来。这一点先按下不表。
太阳落下了山。柳翠要带着儿子回家,皇留口离莲浦还有好几里地呢!突然,她发现师婆在前面向她招手。柳翠原本想不搭理师婆径直回家,但人家向她招了手,就走不掉了。柳翠让儿子站在原地等她,自己向师婆走去。
莲浦村也有师婆,柳翠都认识。但眼前这个师婆柳翠却从未见到过。柳翠来到师婆面前,低头鞠了一躬,问:师傅叫我过来有何指教?
师婆放下右侧臂弯里的柳条篮子,说:仙家,这个东西你可还认得?
柳翠看了看柳条篮子,说:似曾相识,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了。
师婆说:这本来就是你家的东西。
柳翠疑惑地说:我家的东西?那怎么到了你的手里?还有,你刚才叫我什么?仙家?我就是莲浦村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妇,哪里是什么仙家!
哈哈,真人面前别说假话。师婆说,你既然觉得这个篮子似曾相识,其实就已经证明了你的身份。你是柳仙家族的小姐,我说的不错吧!你的母亲当年为了报答条匠张远山的救命之恩,把你许配给他儿子张根奎。这一点我也说的不假吧!
你、你、你怎么知道这一切?柳翠惊慌万状地说。
呵呵,你看看我的装束,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能不知道这些吗?不知道这些还能吃这一碗饭?师婆边笑边说。
柳翠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就算你说得对,不过这个篮子我确实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了。我再问你一次,既然是我家的东西,怎么现在到了你的手里?
师婆说:你们的住处本来离莲浦村不远,但不知道为什么编织的柳条篮子不在莲浦村周围卖,却跑到百里之外的天行庄去卖。天行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柳条篮子。
天行庄?你是天行庄的人?柳翠心里一紧。
是的,我家住天行庄。而且娘家婆家都在这个村。师婆回答。
师婆的话勾起柳翠一段沉痛的回忆。那时她还小,还不记得父亲的模样,父亲就被雷公用雷电劈死。她的妈妈柳老太太用柳条编织成篮子,常常拿到天行庄的集市上去卖。天行庄离莲浦村有百十里地,村子较大,有上千口人,这在太行山深处是一个难寻的大村庄。而且,这个村里有好多大户人家,非常喜欢使用柳翠家编织的小白篮子。遗憾的是柳老太太没有在意“天行庄”这个村庄名字的来历。天行庄里,有天庭玉帝和王母的行宫。每年的夏季,玉帝和王母都要到行宫里住一段时间。正是在那年盛夏的一天,玉帝和王母化为百姓的模样在天行庄庙会上游玩,发现柳翠的父母摆摊出售柳条篮子。因为柳条篮子比荆条篮子精致漂亮,所以尽管价格很高,但购买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而旁边的荆条篮子却少有人问津,人们购买的大多是荆条编的篓子筐子等粗笨的农具。这种情景,让玉帝和王母看在眼里很不舒服,心想,这两个卖柳条篮子的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不顾及同行条匠的死活?按这个卖法,你们撑死了,卖荆条篮子的同行就要饿死了。他们想教训一下卖柳条篮子的人。然而,当他们来到柳翠父母的摊位一看吃惊不小:敢情这两位竟然不是一般条匠,而是位列仙班的柳仙,怪不得他们的篮子编得那么好卖得那么快!玉帝和王母不由勃然大怒:这不是与百姓抢食吃吗?这是触犯天条的罪责,当罚不恕!于是,当面斥责柳翠父母不该在这里兜售柳条篮子,快快收摊走人!
开始,柳翠父母以为碰见了当地的地痞流氓和黑道混混,就没有搭理玉帝和王母,头也没有抬。玉帝见状大喝一声: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柳翠父母这才抬起头来。一看,吓了个六神无主。眼前这两位虽然是老百姓装束,别人认不出来,但他们能认得出来——这是玉帝和王母,天庭的大老板哪!
柳翠父母连忙向玉帝王母解释说:我们本是莲浦村的柳仙,所编柳条篮子从来不在莲浦周围的集市上出售,怕和村里的条匠抢食,所以才来到这一百多里地外的天行庄来卖。这个村子地势比较平坦,也不出产荆条,村里也没有条匠,所以也就不存在与当地条匠抢食吃的情况。
玉帝说:那也不行。你们位列仙班,不去好好修行,在这里摆摊做买卖成何体统?
玉帝的话,柳翠父母听了不以为然,分辨说: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莲浦村一带满山遍野的柳树吐出了嫩芽,正是编织柳条篮子的大好季节。我们有这个手艺,编出柳条篮子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生活方便,这又有什么不好?我们卖篮子挣得钱大多数资助了当地的穷苦人家,这又有什么不好?
然而,无论柳翠父母怎么解释,玉帝和王母就是听不进去,认定柳仙触犯天条按律当死。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雷公电母劈死柳翠父母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是后来柳老太太临死时告诉柳翠的。故而,一听到天行庄这个名字,柳翠心里就不由自主地一震!
柳翠问师婆:你今天走这么远的路从天行庄来到皇留口,难道就是让我看这个柳条篮子吗?
当然不是。师婆说,这个篮子只是个引子。庙会上人多,有些话不方便说,我便用这个篮子把你引到这里来,是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柳翠问。
我想收你做我的徒弟。
怎么?你想让我当师婆?
不错。你意下如何?
不不,我不愿意干这个!柳翠连连摆手拒绝。
师婆说:你的脸上带着师婆相,这不是你愿意干不愿意干的问题。你如果不愿意干,以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一点,相信你也听说过。
这一点,柳翠确实听说过。莲浦村就有些妇女因为不愿意当师婆而三天两头身子不舒服。莲浦一带的村民有个说法,认为师婆和马公都是阴间鬼魂的代言人,他们想向阳间的亲朋好友或仇人宿敌捎话,自己无能力办到,只好求助于师婆和马公。而谁不愿意当师婆和马公,阴间的人就会找他们的麻烦。突出表现就是接连不断地打哈欠。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发笑,打个哈欠算什么麻烦?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吗?其实,不论什么东西太多太滥了就是麻烦事一桩。就比如打哈欠,一个两个无所谓,如果一连几天或数月毫不停歇地打,谁能受得了!打起哈欠来,饭吃不好觉睡不好,什么活儿也干不了,你说难受不难受!
尽管这样,柳翠还是不答应当师婆。正在这时,她的儿子张依柳走了过来,对师婆说:婆婆,我娘不愿意当,我替她当行不行?
柳翠扭头看了一眼儿子,发现孩子的脸色由红润变得蜡黄,像得了重病一样。她不明白这么一小会儿的工夫,孩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不过她也没有多想,或许是儿子本不愿意当师婆,只不过不想让当娘的为难和受罪,甘愿替自己挡这一劫而已。柳翠把依柳紧紧地抱在怀里,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孩子,那个活儿可不好干呀!咱不干。娘不干,你也不能干!
不料,张依柳却说:娘,我愿意干。
柳翠听了吓了一大跳,本想劝说儿子放弃,但见依柳神色坦然自若,没有丝毫不情愿的表情。这时,师婆走到张依柳跟前,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盖骨,又看了看他的十个手指头,连喊几个好,说:这个孩子骨相里带着哩,将来会成为一个好马公!
师婆最后这一句,又让柳翠心头一凛。她想最后再问一次依柳:孩子,你真想干这个营生?这可是个死里逃生、生不如死的勾当呀!
死里逃生、生不如死,自然有点危言耸听。柳翠是不愿意让依柳干这个而故意这样说的。不过这倒也符合师婆马公的职业特点,他们出入阴阳两界,确实是在生死两界的边缘游荡。
娘,我是真心想干这个。张依柳语气坚定地说。
这时候,柳翠发现儿子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平日的红润。既然儿子心意已决,柳翠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那就随你去吧。转而又对师婆说:孩子做师婆可以,但绝对不能做马公。
师婆问:这是为什么呢?师婆马公是一回事啊!
柳翠说:不是一回事。你还非让我把事情挑明了吗?
师婆说:你不妨挑明了说,我听听有什么不同之处。
其他地方的师婆马公我不清楚,但莲浦村的师婆马公我知道。师婆是女性,可以见阴间的人,但阴间的很多地方是去不了的,除非她已经变成了鬼魂,比如阎罗殿。但这个地方马公却是可以进去的。我的儿子虽然不是鬼魂,但那个地方我是坚决不让他进去的。请你理解我做母亲的心情。
听了柳翠这番话,师婆的脸色忽阴忽晴不住地变化,好在此时天色已晚,柳翠并没有看清她的脸色,否则就可能断然否决依柳的意愿。师婆抬头看看天色,说:不早了,你们还有好几里地要走,我的路途更远。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完,提起地上的柳条篮子擓在臂弯里,紧走几步消失在夜色里。
柳翠拉着儿子张依柳往莲浦家里走。她的心很沉重,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踩着棉花团一样。扭头看看儿子,发现他却很高兴,一路蹦着跳着,嘴里还不住的唱着当地流行的山野小曲儿。
回到家,丈夫张根奎也刚从山上割荆条回来。柳翠把在皇留口遇到师婆的事情向丈夫述说了一遍,说自己很不情愿让他干这个。张根奎思索了一阵说:看来我们的儿子就是这个命。你不让他干反倒不好。唉,不管干什么吧,能混一碗饭吃就行。就像我,每天翻山越岭的割荆条,不就是为了一家人有口饭吃吗?师婆也好,马公也罢,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也离不了这些人,既然离不了就总得有人干。
其实,自从张依柳出生以后,村里的师婆就对张根奎说过,你这个儿子骨骼生的奇异,是个当马公的好材料。张根奎知道因为自己身世的缘故,媳妇柳翠不愿意让儿子再与神神鬼鬼打交道,就没有告诉她,也叮嘱村里的师婆不要和柳翠说类似的话。想不到,这次遇到天行庄的师婆,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捅破了也好,纸里包不住火,孩子是这种人,迟早要出这个道。
丈夫的话给了柳翠不少安慰,心里逐渐宽敞了许多。她告诉丈夫,自己已经和那位师婆说好,儿子依柳只当师婆不当马公,就是说只和阴间人见面不下阴曹地府。
张根奎听了没有说什么,心想男人当的就是马公,当马公就要下阴曹地府,这不是你想下不想下的问题。但他怕媳妇伤心,没有明确说出来。
张依柳十五岁那一年,正式出道当了师婆。算是莲浦村第一个男师婆。其实莲浦村里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当着柳翠的面不愿意称呼依柳为马公。
师婆和马公这个营生很特殊。说起来他们和其他匠人一样也有师承,但又没人见他们跟着师父学过艺,似乎当上师婆和马公后,行业里的那套把戏自然而然就会了。就像这个张依柳,小小年纪,又是给人看阴地看风水,又是张罗村民们的丧事。他这一出道,村里的其他师婆们都等于失了业。
那年冬季的一天下午,张依柳挎着粪筐到村外拾粪,忽然看见从村前山上走下来一个人,穿着一身红衣服,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肩头挎着一条大绳。张依柳看着这个人有点眼熟,好像是莲浦村东头刘家大院里的刘延保。怪,这个刘延保平时最爱穿浅色的衣服,怎么今天穿了一件红色衣服呢?更为奇怪的是他拿着镰刀挎着大绳从山上下来,看样子是去山上砍柴。但柴呢?怎么空着手回来了?待刘延保走近一看,天哪!他哪里是穿着红衣服,而是浑身血迹。刘延保从张依柳身边匆匆走过。平日里刘延保见到张依柳就和他开玩笑,可今天却什么也不说,只顾低着头走路。更让人奇怪的是他不是往家里走,而是往下莲浦走去。然而,快走到下莲浦时,他忽然又转身向黄崖方向走去。刘延保这个奇特的举动顿时引起张依柳的警觉。哎呀不好!刚才刘延保从张依柳身边走过时,他看了一下刘延保的脸色,发现白的吓人。他、他肯定是遭遇了不测,说不定是坠崖而亡了,自己看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鬼魂。鬼魂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但张依柳是阴阳两面人,可以看到鬼魂。还有,刘延保刚才不往家走往下莲浦走,而下莲浦是一片坟地。他可能意识到自己不是正常死亡,是不能埋葬在下莲浦的,所以又转身向黄崖走去。前面的故事里说过,黄崖这个地方是专门埋葬莲浦村非正常死亡者遗体的。
张依柳的判断不错。刘延保今天上山砍柴,看到前面悬崖绝壁上有一株粗壮的紫檀。紫檀木是非常珍贵的树种,刘延保想把它砍下来做家具,不料紫檀生长的地方太陡峭,他一个不小心就从悬崖上掉了下去。悬崖高约三十多丈,悬崖下面都是乱石堆,掉下去焉有命在?早一命呜呼了。刘延保摔死的地方离莲浦村有十多里地,碰巧那天他是一个人上山砍柴,连个伙伴也没有,所以村里人特别是刘家大院的人短时间内并不知道他已经遇难。在莲浦村有一个说法,在外面横死的人,其鬼魂是会先回来寻找安葬地的。偏巧刘延保的鬼魂被张依柳撞上了。张依柳顾不得拾粪了,赶紧来到村东刘家大院,告诉刘延保家人,说刘延保已经遭遇不测,要赶紧为他准备后事。
刘家的人初听此言根本不相信,抱怨张依柳无端地咒人死,是想发死人财。这里需要介绍一个情况。莲浦一带死了人办后事都由师婆马公去办理。办完后事,东家要给师婆马公一定的报酬,毕竟处理这种事情是很耗神费力的,而且多半是在夜间办事,风险也大,处理不好,不仅阳间的人不满意,阴间的鬼魂也不高兴。不满意不高兴就会找他们的麻烦。阳间的人找麻烦无非是在日常生活中送点腻歪,阴间的鬼魂找麻烦才是真正的麻烦,真是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张依柳是刚进入这一行,办理此事也只有一两件,但道行却不小。他能在大白天发现鬼魂的行踪,说明在白天他就能出入阴阳两界。在受到刘家人的高度质疑后,张依柳不改初衷,依然劝他们早做安排早些超度亡灵。一般阳间人看不到鬼魂早归,但张依柳却看到了,既然看到了就不能袖手旁观。
果然,直到太阳落山,刘家人也不见刘延保回来,这才托人去山上寻找,最后在一处悬崖下面发现刘延保的尸体,已经摔的血肉模糊,辨不出人形。前文中曾经提及,不是得病而亡的人属于横死,横死主凶,一般师婆和马公不愿意办理横死之人的丧事。但张依柳却接下了刘延保的丧事,一来刘延保只比张依柳大四五岁,生前两人关系很好;二来冥冥之中刘延保的鬼魂返回时似乎是故意让张依柳看见的;三来张依柳也想借这件事情扬扬自己的名气,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得干好,他的敬业精神很不错。
莲浦村的丧葬习俗,得病死亡的人“小三天”下葬;非正常死亡的人“大三天”下葬。“小三天”是指从死亡之日算起,第三天凌晨埋进坟地里去;“大三天”是指从去世之日的第二天算起,三天后即死亡的第四天凌晨下葬,目的是用更多的时间为死者做法事,更好的超度亡灵。莲浦村东刘家是大户人家,很有钱,破例做了五天法事。在这五天里,每晚间十二点左右,张依柳都要领着刘家的人到村外去为刘延保招魂和送花红钱。送花红钱可能有些读者不懂,就是给死者往冥间银行存款。招魂和送花红钱时,张依柳让刘家的人跪在离自己两丈远的地方,低下头不许出声。这时,张依柳就进入了阴间与刘延保的阴魂进行了对话。张依柳对刘延保说:你已经隔世为人,有什么吩咐家人的,请对我讲,我会代为转告。刘延保说:我还不满二十岁就遭此横祸,实在不甘心。请你转告我的家人,万万不要再到那处悬崖上砍柴,万万不要再砍那株紫檀。那株紫檀是不祥之树。
刘家的人只听见张依柳在窃窃私语,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过了一阵,张依柳轻轻喊了一声:大家抬起头来吧。刘家人抬起头,张依柳告诉他们:延保刚才说了,告诫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悬崖上砍柴,不要再砍那株紫檀。事后刘家人曾悄悄到那处悬崖上看过,果然有一株粗大的紫檀,就是这株紫檀要了刘延保的一条年轻的性命(这株紫檀以后的故事里还会提到)。
……
五年以后,张依柳也到了刘延保这个年纪。有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对张根奎和柳翠说:爹,娘,我想出一趟远门。
张根奎问:你要到哪里去?
柳翠也问: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
张依柳说:我去的地方很远,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柳翠一听,着急地说:儿啊,要是那样娘是不让你去的!
张依柳说:娘啊,这事您做不了主。是阎王爷让我去的。
张根奎听明白儿子的意思了,敢情他是要死呀!就上前紧紧地搂住依柳说:孩子,你活得好好的,怎么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来?你是不是闹了什么病说胡话呢?他用手试了试依柳的脑门,也不发烧呀!
吃过饭后,张依柳拿出平时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服穿在身上,静静地躺在炕上,嘴里不住地说:愿二老长命百岁!
张根奎和柳翠搂住儿子不住地啼哭:我们活了好几十岁了,你可刚到二十岁呀!爹娘去和阎王说,我们宁愿现在就死,也要让你多活几年哪!
张依柳说:二老不要为我难过,我就是这么大的寿数。我是一个马公,曾做过一件折寿的事情,所以阎王爷不容我。我死后,二老可以活到耄耋之年,这也算是儿子应尽的一份孝心吧!
张根奎说:孩子,我越听越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柳翠也说:你不是个师婆吗?怎么成了马公呢?当年在皇留口,我亲口和那个天行庄的师婆说过的呀!
张依柳说:您确实和人家说过,但人家并没有答应。男人既然干这行那就是马公,不会是师婆。娘,你还记得当年你曾发现我的脸色蜡黄吗?
柳翠回忆了一下,说: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脸变成那个颜色。
张依柳说:那我现在告诉您好了。接下来他告诉张根奎和柳翠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原来那天擓白色小篮子的老太太招手把柳翠叫过去时,只留下张依柳在原地等着。一会儿,有个男人来到他跟前说:孩子,你在这里等谁呢?
张依柳说:等我娘。她在前面和那个老婆婆说话。
男人说:我带你到个好玩的地方看看,好吗?
张依柳正是贪玩的年龄,就说:好!
男人抱起张依柳往旁边一个岔道上走。走着走着,张依柳觉得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了。等他醒过来时已经来到一个大殿里,里面阴森森的非常恐怖。
男人说:这就是阎罗殿,你以后要常来常往。
张依柳害怕地说:我不愿意来这里,我要回去找我娘。
男人说:你以后会当个出色的马公,我先带你来认认路,一会儿就回去找你娘。记住,这件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任何人说。
奇怪,男人说过这句话后,张依柳忽然觉得不像刚才那样害怕了,大殿里也不像那么阴森森的了。
回来后,因为心有余悸,所以柳翠看到儿子脸色蜡黄,过了一阵他的脸色才恢复正常。
大约半年前,张依柳因为给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招魂来到阎罗殿。阎王说你自己看看生死簿上有这个人的名字吗?
张依柳没有发现这个人的名字,却在上生死簿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爹娘的名字。天哪!名字出现在阎罗殿的生死簿上,那就活不了几天了。不能,万万不能让爹娘死!于是,他偷偷将爹娘的名字抹了去……于是张依柳触犯天条,犯下了死罪。
张依柳死了,但张根奎和柳翠真的都活了将近百岁。
……
张老顺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明显有点累,喘着粗气点燃一袋烟,“呼哧呼哧”地抽了起来、
我却有些意犹未尽,问:这集故事显然是天行庄的师婆和那个男子合伙做局让张依柳上套,让他年轻轻地送了一条命,有点残酷。
张老顺说:不错。不过这也是张依柳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还好,他为爹娘赢得好多年的寿数。
我觉得师婆和那个男人出现的突兀,你好像没有交代清楚。
张老顺咧嘴一笑说:交代的太清楚了,下一集说什么?
原来如此。那下一集说什么?我饶有兴趣地问。
张老顺说:还返回匠人的话题,咱们讲《毛毡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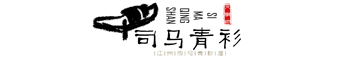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