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顺说这一集讲《毛毡之家》,我有些着急,因为听起来好像与天行庄出现的那神秘的一男一女关系不大,我很想知道那一男一女的身份由来。
张老顺有点不悦,说:不要着急,迟早总要让你知晓的。讲莲浦村的鬼怪故事,我自有我的套路,希望你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我就不敢再讲什么,只好顺着张老顺的思路说:你在前几集里提到莲浦村的毛毛匠,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毡之家就是毛毛匠之家。
你只说对了一半。张老顺说,我在前几集里讲过,毛毛匠是个统称,可以细分为两个行当:一个是做毛毡的匠人,比如莲浦村炕上睡觉铺的大毛毡,冬天生火取暖的火盆下面垫的小毛毡,还有男人头上戴的毡帽壳等等。另外一个是做装粮食用的毛口袋的匠人。无论是毛毡还是毛口袋,因为所用原料都是羊毛,所以都叫毛毛匠,但毛毡和毛口袋的制作方法却大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我问。
听你这样问,我推断你一定没有见过毛毡和毛口袋。张老顺说。
我讪讪地回答:对,我确实没有见过这两种东西。
这也难怪,你是城里人,用不到这些东西。这样吧,咱们先不讲故事,我先领着你去见识这两样东西行不行?你有没有兴趣?张老顺问。
那再好不过!我说着,就催促张老顺赶紧领我去看。
张老顺站起身来,把烟袋锅往腰里一插,说声:走!再过几年,恐怕我也见不到这种东西了。
我问:那又是为什么?
张老顺说:现在人们铺的盖的都换成羽绒的了,又轻巧又暖和,谁还用那些沉呼呼的毛毡?而且现在装粮食也都用蛇皮袋尼龙袋,谁还用毛口袋?
说话间,到了村西一间屋子前。张老顺从兜里掏出钥匙开开房门,用手一指,说:你看,那就是毛毡和毛口袋。
我抬眼向屋里一望,里面果然堆满毛毡和毛口袋,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大的有小的,但大都是新的。
我不解地问:这是谁的屋子?怎么里面放着这么多毛毡毛口袋?
张老顺说:屋子嘛,可以说是我的,也可以说是生产队的。
我又不明白了,问:如果是你的,那是私人财产;如果是生产队里的,那就是集体财产,两者是不能混肴的。再说,你的家不是在村东头吗?怎么村西还有你的房子?
张老顺听了哈哈一笑,说:这是生产队里专门给我盖的放毛毡和毛口袋的房子。毛毡毛口袋也是生产队里专给我制作的。
为什么专给你弄这些东西?我大惑不解,一个看羊的瘸腿老汉,竟有如此高的待遇。
张老顺说:看羊是个苦差事,晚上露宿在野地,风里来雨里去。村里怕我着凉受寒受潮,规定每年给我做一领新毛毡和两口新毛口袋。其实我用不了这么多,我现在铺着的毛毡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
我问张老顺:毛毡是怕着凉铺在身子下面的,这一点我理解。但毛口袋是装粮食的,生产队里给你做这么多毛口袋干啥用呢?
张老顺神秘一笑,说:当然有用,这个以后再讲。莲浦村匠人很多,你知道我最熟悉的是哪类匠人吗?
那类匠人呢?我皱着眉头说。
毛毛匠。
为什么是毛毛匠?
张老顺说:毛毡毛口袋的原料是羊毛,而我就是看羊的,所以说,毛毛匠的故事与我包括羊倌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不过,羊倌放羊是白天的营生,发生故事较少,大多数故事发生在夜间。所以说,我张老顺与毛毛匠最贴近;毛毛匠的故事也与我关联最密且。
在这间堆满毛毡毛口袋的屋子里,张老顺对我讲了毛毡之家的故事。
这一家人住在莲浦村北,男主人姓孟,叫孟传祖。当地方言把“孟”常常念成“冒”,所以人们有时候就叫他冒传祖。他也是个外迁户,早年间姓孟的先祖从遥远的北方迁到太行山深处落脚为生,就把毛毛匠手艺也带到了莲浦一带。又因为姓“冒”,所以莲浦人就习惯的称其为毛毡之家。毛毡之家是个统称,其实是两户人家,兄弟俩分了家,哥哥孟传祖一家专做毛毡;弟弟孟传宝一家专做毛口袋。因为莲浦一带毛毡用量很大,于是人们又往往把孟传祖这一支称为毛毡之家。我们这一集专讲毛毡。
讲毛毡故事之前,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毛毡制作方法。毛毡看起来平平常常,但其制作工序比较复杂。先是从羊身上剪下羊毛来,再把羊毛弹成绒状物,最后通过加水、加热、加压使其浓缩为方方正正的毛毡。做毛毡一般是在三伏天,气温越高越好,这样可以使羊毛更加柔软。所以,我看羊是个苦差事,做毛毡也是个苦差事。我要经得住夜间的冷,而他们要经得住白天的热。
张老顺讲到这里,我插话说:据我所知,羊身上有很厚的羊绒。每年农历三四月份天将热时,人们就会把羊绒弄下来。羊绒要比羊毛暖和的多也值钱的多,用它做毛毡不是更好吗?为什么硬要费时费力的把羊毛弹成羊绒?
张老顺说:用羊绒做毛毡当然好,但太奢侈。在莲浦村,羊绒往往被拿到集市上卖大价钱补贴家用,谁舍的用它做毛毡?据说,羊绒都被都市人纺成毛线织毛衣穿在身上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点头称是。
张老顺接着讲他的故事。
因为白天羊群要上山吃草,所以剪羊毛大都是在月光明亮的夜间进行,一般是孟传祖带着家人来到羊卧地的地方,根据用户需要,挑选出几只个头较大的羊,将其放倒,用绳索捆住四肢,用剪刀轻轻将羊毛剪下来,不能伤及羊的皮肉。俗话说,好夜间比不上赖白天,晚上的月光再好,也不如乌云密布的白天看的清楚。张老顺天天晚上看羊,练就了一双“夜眼”,比一般人视物清楚,所以孟传祖经常让张老顺帮忙剪羊毛。
这天夜里,月光如水。一百多只羊安安静静地卧在一块平坦的地面上。白色的羊,莲浦村民称之为绵羊,黑色的羊称之为山羊。羊群黑白相间,相互点缀,犹如一幅美术作品,甚是美观。张老顺坐在小窝棚里,嘴里叼着旱烟袋,眼睛端详着这幅美丽的画图,悠然自得。他在等待着孟传祖一家的到来。今天下午,孟传祖告诉张老顺,晚上自己一家要来剪羊毛。莲浦村有个小伙子要结婚,女方要的彩礼中包括一白一黑两领毛毡,是送给女方父母的。要在平日,黑灯瞎火的孟传祖就不来了,打发儿子姑娘来就行了,但这次不行,是姑爷送给老丈人丈母娘的礼物,要求原料最好手艺最好,制作出来的毛毡质量也最好。所以,孟传祖就亲自出马,并且让老朋友张老顺务必帮忙。
半袋烟工夫不到,地头来了四五个人,领头者是个大高个。月光下虽然看不清楚来人的脸面,但张老顺知道是孟传祖来了,因为孟传祖是莲浦村第一高个,足有一米九。于是,他连忙从窝棚里探出身子,喊了一声:传祖老弟,我等你多时了。
要在以往,听到张老顺招呼,孟传祖会回应一声:哎呀,不好意思,让老哥久等了!然而,让张老顺颇感意外的是,今天晚上,高个子孟传祖竟没有说这一句话,而是带着家人来到羊群中间,放倒几只羊,就急匆匆地剪起羊毛来。张老顺虽然感到情况有点反常,但也没有多想,认为孟传祖可能是东家货要的急,没有时间和他打招呼,情有可原嘛!想罢,张老顺就从窝棚里抽出剪刀,也放倒一只大绵羊,“嚓嚓嚓”地剪起羊毛来。
大约一个时辰,孟传祖带来的几条毛口袋里都装满了羊毛。他和几个子女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碎羊毛,准备离去。过去剪羊毛,张老顺和孟传祖常常是边剪边交谈,有说有笑很是热闹。但今天晚上,孟传祖只顾自己忙活,始终没有和张老顺说过一句话。孟传祖不说话,张老顺也不好意思无话找话,只好闷着头剪羊毛。直到孟传祖把毛口袋扛到肩上迈腿要走时,张老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孟传祖:老弟,什么事情急成你这个样子?连和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孟传祖听了,愣了一下,撤回已经迈出去的脚步,不冷不热地小声说了一句:擀毡。说完,领着家人头也不回地急匆匆走了。
擀毡?张老顺听了也是一愣:这个名词好熟,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对了,在莲浦村往西北一百多里地外的山西省地界,人们管制作毛毡就叫擀毡。可莲浦村自从姓孟的这个毛毡世家来了后,从来没有用过擀毡这个叫法,多是用“做”或“弄”等。他们是毛毡世家,难道不知道这个“檊”字最形象最准确吗?
孟传祖的反常举动,特别是不冷不热的态度,让张老顺长时间想不明白,就不住地“吧嗒”着抽烟。莫非是我哪件事情做得不对得罪孟传祖了?他前思后想实在想不出在哪里得罪过他。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张老顺大了两个哈欠。算了,不想了,抓紧时间睡觉吧。
刚要入睡,忽听窝棚外传来一声喊:老顺大哥,你睡下啦?
这个声音张老顺再熟悉不过了——是孟传祖的声音。张老顺寻思,看来刚才他慢待了我,觉得难为情了,这是向我道歉来了。嘿,这个孟传祖,道歉也不差这一时半晌呀,明天再道歉也行呀,这大半夜的!再说了,咱们一村当院住着,哥儿们关系又不错,还用得着道歉吗?于是,张老顺没有起身,躺着身子喊了一声:传祖老弟,天不早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明天?明天要误事的!窝棚外又传来孟传祖的喊声。
我不怕误事!张老顺还是没有起身。
你当然不怕了,你黑夜看羊白天睡觉,能误什么事?可我怕误事,到时间我交不了活儿,耽误人家的婚姻,还不挨骂一辈子?到那时,我这毛毛匠也就别当了!孟传祖的喊声越来越高。
张老顺有点迷糊:你不是已经剪过羊毛了吗?明天你就可以做毛毡了,顶多两三天就可以把活儿赶出来,怎么能耽误事呢?
张老顺正想着,孟传祖已经来到小窝棚前。张老顺抬头一看,孟传祖手里拎着一条大号毛口袋,后面跟着他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每人手里也拎着一条毛口袋。
看到这个架势,张老顺愣了起来,问:你、你、你们这是要干啥?
干啥?剪羊毛啊!咱们下午不是说好了吗,你得给我们帮忙,这可是你答应过的,怎么?忘了?
原来是让我帮他剪羊毛,不是来道歉的。张老顺爬起身子,对孟传祖说:你们刚才不是已经来剪过羊毛了吗?怎么又来剪?就那么几领毛毡,用得着剪那么多羊毛吗?
你说什么?刚才?刚才谁来剪过羊毛?孟传祖也一愣,惊讶地问。
你呀!你刚才领着几个孩子来,我还帮你剪了一阵。我的眼神不好,差点剪破我的手指。
老顺哥,你在做梦吧,我刚才没有来呀!吃过晚饭后,我老婆突然肚子疼了起来,我带她到皇留口周医生那里去看病,刚回到家,怕耽误人家的活儿,这不,后半夜了,也得把羊毛剪回去,要不明天开不了工。
你说的是真的?虽然觉得孟传祖说的有来有去有鼻子有眼,但张老顺还是不太相信,刚才孟传祖来剪羊毛明明是自己亲眼所见嘛,怎么他非说没有来过呢?
当然是真的,我啥时候糊弄过你呀!我在莲浦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谎话,何况你还是我的好朋友呢!
这就怪了,那这帮人又是谁呢?张老顺自言自语地说。他边说边下地取出剪刀领着孟传祖来到羊群边,用手指着已经偏西的月亮,对孟传祖说:就在月亮刚出东山岗不久,我见你领着孩子们来到这里。你看,就是这几只羊。张老顺随手抓过一只绵羊,又说,这只羊的毛就是我剪的。
见张老顺同样说的有来有去有鼻子有眼,不相信也由不得自己了。孟传祖纳闷了,心想:一定是有人冒充了我来剪羊毛。可究竟是谁冒充我呢?这个人剪羊毛又是为了什么呢?莫非也做毛毡?可莲浦村只有我孟传祖一家做毛毡呀!难道是别村的人来偷剪羊毛?如此这般想着,他的双手就不由自主地摸了摸眼前这只大绵羊。这一模,让他大吃一惊,忙问:老顺大哥,你说自己剪的这只大绵羊?
张老顺说:是的,我剪的就是这只大绵羊。
孟传祖说:你是用什么剪的?
张老顺说:当然是用剪刀呀!说着,晃了晃手里的剪刀。
孟传祖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嘿嘿,你自己摸摸,这毛不还是好好地长在羊身上吗?哪里剪掉了?
听孟传祖一说,张老顺赶紧去摸,嗨,毛果真好好地长在羊身上,哪里有剪过的痕迹!奇怪,当时我可是一剪一剪地剪下来的呀!剪下的羊毛我又一把一把地装在毛口袋里,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人扛着口袋回到莲浦村。可现在……紧接着,张老顺又把那几个人剪过的羊也一只一只做了检查,天哪,天底下还有这种稀罕事情发生吗——这些羊的毛都好好地长在身上,半根都不少啊!
这时,孟传祖若有所思地对张老顺说:显然是有人冒充我来过这里。老顺大哥,这几个人都长什么模样?
张老顺说:那个高个子的人和你一样,他那几个孩子也和你的孩子差不多。你也懂得,我常年夜间看羊,习惯于夜间视物,自认夜间视力要比你们强一些,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他当成你。
孟传祖想了想,又问:这个人说什么话了没有?
张老顺说:剪羊毛的时候,他一句话没有讲。我问他,人家也不接话茬。临走时我又问他,他只说了一句:擀毡。
什么什么?他说擀毡?老顺大哥,你有没有记错?你确定他说的是擀毡两个字?孟传祖忽然变得很激动,语气显得特急促,刚才的慢条斯理霎时跑的无影无踪。
就是这两个字。传祖老弟,我虽然比你大几岁,但还远没有到耳聋眼花的地步。这两个字我是听的真真切切的,绝对错不了!张老顺信誓旦旦地说。
难道是他、他来了?孟传祖一只手托着下巴,像是对张老顺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他是谁呀?我看这个人和你一个模样,该不是你的什么孪生兄弟吧?张老顺试探着问。
孟传祖还在思索着自己的问题,好像是没有听见张老顺的问话,故而没有回答。
张老顺也急切地想弄清楚这个人是谁,见孟传祖没有回答,就又问了一次。
这次孟传祖听清楚了,就说:老顺大哥说的差不多,这个人或许应该是我的兄弟,但肯定不是孪生兄弟。
这叫什么回答?什么叫或许应该是自己的兄弟?这传祖老弟平时说话挺干脆的嘛,怎么今晚要绕这么大个弯子,快把人绕糊涂了。张老顺想。
大概孟传祖也觉得自己的回答太拗口,就解释说:此事说来话长,大哥容我以后慢慢解释。我现在觉得奇怪的是,如果真是他,那他就是特地来找我的。可他找我又有什么事情呢?
找你?那他怎么不到你家里找,非要在深更半夜到这个荒郊野外来找?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剪羊毛,这不是故弄玄虚吗?张老顺说。
张老顺这番话听到孟传祖耳朵里,孟传祖心里突然一紧!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那只大绵羊,突然,他明白过来,刚想叫出声来,然而转头一看跟前的三个孩子,又连忙用手捂住嘴巴,强行把蹦出的话头咽进了肚里——他怕吓坏孩子们,特别是小女儿才十来岁,平日就胆小的厉害,天一黑就不敢出屋门。现在已经是后半夜,她一旦知道父亲说出那几个人的真实身份,肯定会吓个魂飞魄散。
孟传祖的举动,张老顺一一看在眼里,知道这里面有了“鬼打刀(莲浦方言:闹鬼的意思)”。他本想讲出来,也是担心吓着几个孩子而没有张嘴,只是对孟传祖说:天不早了,咱们快剪羊毛吧,别耽误了你天亮后用。
孟传祖说声“是”,就手放倒身旁的大绵羊,抽出剪刀,“咔嚓咔嚓”地剪起羊毛来。
月亮快落下西山时,孟传祖扛着装满羊毛的口袋,领着三个孩子准备回村。这时候,张老顺摸了摸剪过毛的几只羊。孟传祖笑了笑说:老顺大哥放心,剪过这一次,这些羊起码要半年后才能把毛长起来。
张老顺明白孟传祖的意思,他是说你不用摸,这次的羊毛是真正剪掉了。这时,他对三个孩子说:你们先回去,我和你爹有几句话说。
孟传祖也正想和张老顺谈谈前半夜的事情,就跟着张老顺钻进小窝棚里。他问张老顺:村里人都称你是半仙,难道你真没有看出那些人——不,他们都已经不是人,而是一缕幽魂。你难道真没有看出来?
张老顺惋惜地说:唉,不满老弟说,我还真没有看出来,这就叫“马有失蹄人有打眼”,不过也有原因。
什么原因?孟传祖问。
因为你说晚上要来剪羊毛,到约定时间真就来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我就没有怀疑。如果咱们没有约定,突然冒出这么一帮人来,我自然是要怀疑的。不管是人是鬼,只要被我怀疑上了,哪怕他伪装的再好,也别想在我面前蒙混过关。
孟传祖笑了笑,心想,这个张半仙,明明今晚打了眼,还非要把面子找补回来。不过,眼前这个事情,还真需要这个张半仙帮忙。于是,他就接着张老顺的话茬说:谁说不是呢?都说你是半仙,我看你就是一个整仙!
张老顺哈哈一笑,说:你老弟也别奉承我。说吧,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提,为兄绝不推辞。
痛快,老哥既然这样说,我也就不推辞了。今天晚上那个人来这里估计是先给我送个信,可能有重要事情和我说。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来,也无法和他联系。老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就代我约他一次呗!孟传祖说。
这有何难?为兄应下了。唉,我就是个看羊的,腿也不方便,给乡亲们也办不了别的事情,只有这件事可以代劳。这么着吧,明晚月亮上来时,你在这里等着,我想法把那个人请来。张老顺说。
好,一言为定。孟传祖谢过张老顺,起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月亮刚刚爬上东山顶,孟传祖就早早来到张老顺的小窝棚前。他探头一看,张老顺没在窝棚里。这个半仙跑到哪里去了,莫非把我所托事情忘了?他正在着急,却见羊群南边上来一个人,走到跟前一看,正是张老顺,手里拿着一沓黄表纸,不住地用袖口擦拭脑门,好像额头上出了汗。
孟传祖问:老顺大哥干啥去了,累成这个样子?
还能干啥?给你请人,奥,不对,请神,也不对。我、我给你请鬼去了呗!张老顺边说边不停地擦拭头上的汗珠。
孟传祖奇怪地问:过去听你说过,烧烧纸,念叨念叨,他们就来了,应该不费多大劲吧?怎么今天看你好像跑了好几十路一样,累的大喘气。
唉,别提了。今天这事真怪,按原来的方法居然不灵验了。
怎么不灵验了?
张老顺说:当我点燃黄表纸时,还没有念叨,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眨眼工夫,我的面前就多了四个人,应该是那个高个子领着三个孩子,和昨晚一样。
骑马的声音?孟传祖听了心里有了数,断定就是那个人。他对张老顺说:他们既然来了,省了你劲了,为什么反倒满脑门汗珠?
张老顺说:对方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呜里哇啦的,好像是外语。我说的话他们可能也听不明白,你说急人不急人!怎么鬼还会说外语?
昨天晚上,他不是说了擀毡两个字吗?这个你懂啊!孟传祖
是啊,偶尔有一两个字也能听懂,但他却是新媳妇放屁——零崩,和整句话就串连不起来。无奈,我们只好打手势,比比划划折腾了半天,我最后才明白,那个家伙说在前面等着,让你过去。张老顺说。
孟传祖知道,那个人说的是北地大漠的匈奴话,张老顺又怎能听得懂?于是,他顺着张老顺手指的方向,向羊群的南边走去。南边是一个侧坡。孟传祖看到侧坡下面站着一个高个子人,身边围着三个低个子的人,似乎年龄都不大。
见到孟传祖到来,高个子又呜里哇啦了几句,孟传祖明白这话的意思: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应该把孩子们也带来,你看我的孩子们都来了。
孟传祖也呜里哇啦地回了几句话,意思是:我的孩子们胆子都小,见到你们害怕,故而没有来。
高个子说:都是家里人,莫非我还能祸害他们不成?你回去把他们都叫来吧,我有话对你讲,也是对我们两家的孩子们讲。
孟传祖点点头,让高个子稍等片刻。他回去把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叫来。正好,高个子身边也是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人齐了。高个子让三个孩子给孟传祖跪下,说:这是你们的祖伯,行个礼。三个孩子给孟传祖磕了三个头。孟传祖上前一步把孩子们搀扶了起来。当他的手臂挨着孩子们的手臂时,奇怪地“嗯”了一声。
这一声虽然很轻,但还是被高个子听得清清楚楚,说:祖弟,我是鬼魂,这三个孩子可是活生生的人哪!说完,也屈膝向孟传祖跪下一条腿,幽幽地说:祖弟呀,先祖对不起你们。当年先祖驾崩之际一再嘱咐后人找到你们,请求你们的宽恕和谅解。不料这一找,竟然找了两千年。还算不错,终于找到你们了。
你怎么不在人世了?孟传祖问。
高个子说:在找你们的路上,我染上风寒不治而亡,但寻找你们的念头始终没有变。我把孩子们带来,就是让他们知道当年的那桩公案。这些事情,过去我和孩子们说过,但他们不相信,就只好带着他们找你们了。
高个子喘了口气接着说:这也就是我让你也把孩子们带来的缘故,要让下一代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要再为此事纠结不清。
孟传祖伸手把高个子拉起来,淡淡地说:我没有为这件事情纠结过,也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讲过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多少年多少辈子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高个子说:还是让晚辈知道的好。我们也都是前辈的晚辈,不是一直都想搞清楚这件事情吗?这次见你,请求你原谅的同时,我还想向你说明一个真相,当年你的先祖逃到长安城后,我的先祖曾多次派人去找你的先祖,不是要斩杀你们,而是想让你们回来……
孟传祖听了高个子这番话,不置可否,仍旧淡淡地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不提也罢。突然,他问高个子,你说找了我好多年,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高个子说,你的先祖在长安怕我的先祖去追杀,后来就逃出了长安。先祖猜测,你们只有往南逃不可能往北逃,所以我们祖祖辈辈就往南寻找。太行山山高林密,战乱年代,好多人为了躲避灾祸而藏匿在太行山深处,于是我就来到太行山里找。那年我找到天行庄,正好碰到一对师婆和马公给一户人家做法事。他们身下铺垫的毛毡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块毛毡很眼熟,像我们家族的手艺,于是我就向他们询问,他们说毛毡出自莲浦村毛毡之家。我问这个毛毡之家姓啥?他们说姓冒,我心里一动,看来这个毛毡之家肯定是我要找的人,于是就来到了莲浦村。
我姓孟,这一带方言很浓,听起来好像是冒。说着,孟传祖也跪下给高个子施了个礼,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给我们道歉,可算是至真至诚。至你说的那个真相,因为年代太久远了,究竟是真是假也无所谓了。有劳你们这么远来找我,感谢了!
不必谢。了却了这件心事,我问心无愧了。祖弟保重!说完,领着几个孩子走了。
张老顺在小窝棚里抽着烟,听着南坡方向不时传来呜里哇啦的声音,等了好长时间才见孟传祖带着孩子们回来,却不见了高个子等人,就问:他们呢?
孟传祖说:走了。
现在该我问你了。张老顺说,这是个什么人呢?奥,现在应该说他是个鬼,但活着时是个什么身份呢?找你来干什么?
孟传祖长长地叹了口气后,说了长长地一段话。原来,孟传祖并不姓孟而是姓挛鞮,远祖是匈奴冒顿单于。冒顿的孙子军臣单于公元前127年去世后,其弟左谷蠡王伊稚自立为王,害的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逃往长安投降汉朝,汉朝封其为涉安侯,数月后突然去世。孟传祖就是于单的后人。当时传言于单是被伊稚追杀而死。孟传祖的祖先害怕伊稚继续追杀,就逃出长安一路南下。逃亡路上死的死亡的亡,到了孟传祖的曾爷爷这一辈躲避到了莲浦村。
作为游牧民族的一员,孟传祖祖祖辈辈都会擀毡,在草原大漠,他们的住所就是毛毡做成的。只是因为其先祖是被伊稚赶走的,所以孟传祖这一支人非常忌讳这个赶字,连其同音字擀字都不愿意说,而都说是做毛毡。
按高个子的话说,伊稚赶走于单后有些懊悔,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于是就派人接他们回去,不料于单已经死在长安,族人四处逃难不知去向。伊稚临死时立下遗言,要自己的后人一定要找到于单的后人,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高个子来之前,孟传祖曾梦见祖先告诉过他,过段时间有人族人找他,但没有说什么事情。他起先以为不过是个梦而已,就每当回事。等张老顺把见到高个子的情况告诉他,他才意识到,这个人可能就是梦里祖先说的那个人。
说到这里,张老顺插话问:那高个子叫什么名字?
孟传祖说: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以我们现在的血缘关系已经远的无法计算了,他爱叫他就叫啥吧。况且他已经隔世为人,我也不能问了。不过跟着他的三个孩子都是活生生的人。
张老顺说:你怎么证明他们是活人?
孟传祖说:我拉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胳膊都是热乎的,而高个子的臂膀却是凉的。
对,活人身上是热的。但那晚剪羊毛,怎么那几个孩子剪过的羊,身上的毛依然好好地呢?我也是个大活人,怎么剪过的毛也好好地长在羊身上呢?怪!
孟传祖笑笑说:鬼打刀鬼打刀,不怪还叫鬼打刀吗?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呀!
张老顺一思忖,确也是这么个道理。忽然,他想起天行庄的师婆和马公,就是那一男一女,他们居然与高个子有一面之缘,看来不是两个简单人物。
孟传祖点点头说:我也这么认为,估计他们以后还会出现。
……
这个毛毡之家不简单哪,居然是冒顿的后代!我唏嘘着说。
谁说不是呢!张老顺也唏嘘着。
天行庄出现的师婆马公就是那神秘听下一集吧。下一集咱们讲《如影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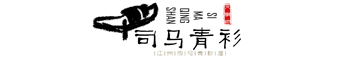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